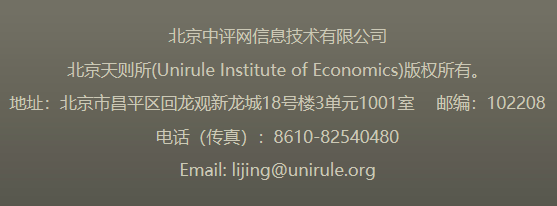湖北省长李鸿忠因抢记者的录音笔、事后又不道歉,遭到媒体的口诛笔伐,一时似乎成为天下罪人。这在我看来并不公平。因为这种行为并非李鸿忠独有,而是一种普遍的、由来已久的政治风气。君不见昆明城管粗暴执法,事后处置了一些城管人员,却不见一句向被打人员的道歉;君不见黄川镇因野蛮诉迁,逼使父子双双自焚,事后赔偿90万元,却也不见一声道歉。然而,我们还是不能责怪他们。
就在李鸿忠事件发生的同一个两会期间,发生了一件比李鸿忠的表现恶劣得多的事情,公众和传媒却视而不见。当记者就《选举法》修改问李肇星,现在将城乡选一代表的比例从以前的四比一改成一比一,是否意味着以前是不公平的,他回答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合理的;当然现在改过来,也是合理的。这个句式我们听着很耳熟。其实,李鸿忠所使用句式也是如此:当时抢记者的录音笔是合理的,后来还了也是合理的。所以,不需要道歉。
只是李鸿忠所抢的东西,与《选举法》所抢的东西不一样。一个是直观的物质器械,一个是并不那么直观的权利;时间长度也不一样,一个只抢了半天,一个却有几十年。可叹的是,我们的传媒更容易看到、或更看重物质器械,而不太关注人的权利;更注重短期内发生的事情,而对长期存在的不公正现象却太麻木。大家对李鸿忠群起而攻之,却对《选举法》的修改缺少应有的热情。
当然,我的这个批评也有点不公正。实际上,这都源于我们这个社会至今没有对文化革命时期极左路线留下的传统进行认真反思。文革以及文革之前整了那么多人,到后来绝大多数人都被平反了,但很少有人出来说一句"对不起"。即使那些被平反的人,往往会被警告说,现在给你平反是对的,过去整你也是对的。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这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句式的经典形式。
仔细想想,从不道歉的行为反映了一种极端错误的认识,它的典型形式就是文革时期的将人当作神来崇拜的痴狂。如果把一个人当作神,他就永远正确,就不会犯错误,所以就没有必要道歉。文革结束后,中共中央对这种个人崇拜的扭曲做了纠正。陈云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会犯错误,他领导的文化革命就一个严重错误。只可惜,这种纠正并没有在全社会产生普遍影响,那个从不道歉的传统并没有被打破。
今天的中国社会,从上到下,无论朝野,都有着远大的社会理想。执政党发誓要"执政为民"。但是且慢。我们还是要从学会道歉开始。道歉之口难开,美好政治之路难迈;"对不起"三字易说,需知其中道理深刻。
会道歉意味着敢承当。道歉意味着道歉者宣称他承担错误的直接或间接(领导)责任,也意味着他愿意接受由此产生的惩罚。这样的领导人或官员才真正值得信任。因为那种"有荣誉就上,有责任就让"的官员是不可能为公众提供优质服务的。
会道歉说明承认自己是凡人,会犯错误,但决心有错就改。公众不会梦想领导人或官员是神或完人,他们能够原谅因人的弱点和局限性而导致的一时错误。历史也告诉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那些知错不改的错误。而道歉,就是一个改正错误的宣言。
有人会说,道歉可能会损害领导人的威信,让他以后不好再担任领导工作。此言大错。古往今来,会道歉从来就是一个优秀政治领导人的重要品质。马踏麦田违反了军纪,曹操割发代首;马谡失街亭,诸葛亮自贬三级。
即使是最高政治领导人,我国从来就有道歉的传统,即《罪己诏》传统。例如汉武帝晚年意识到自己过度倚重军事征伐,导致民不聊生,就发布了著名《轮台罪己诏》。其中说道,"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由于汉武帝能够"罪己",及时纠正了以往的错误,使得他"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司马光语)。
可以看出,能否道歉决非生活小事,而是一条重要的政治文化原则。当初毛泽东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周期律的提问时说,我已找到答案,这就是"民主"。在今天,民主在中国虽有发展,却艰难前行,还不能有效施行。我们还要借助于中国自古以来的这一政治文化传统。其实,有关"兴""亡"之说比较完整的表达是《左传》所记,出自鲁国正卿臧文仲之口:"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变迁的因素多种多样。臧氏竟然将兴亡更替的关键因素仅归结为是否道歉,实在令人惊奇。但细细想来,还是颇有道理。我们知道,就社会演进的方式而言,经验主义要优于建构主义。从经验主义的历史观来看,人类发展的最好方法就是试错,也就是"错了就改"。但是能否改,取决于是否承认错误。因此,在会道歉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社会会迅速崛起;在不会道歉的领导人的带领下,一个集团会转瞬衰亡。这已被中国历史所证明。
实际上,道歉原则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与民主制度的互补,可以成就一个长治久安的繁荣社会。聪明的选民知道,一个会道歉、愿意承担错误责任的领导人,要比一个宣称自己一贯正确的领导人更可靠。
2010年4月9日于五木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