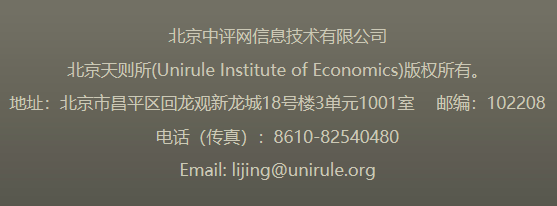南方周末:作为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中国学者,您对威廉姆森获奖有怎样的感受?
盛洪:不意外。他获奖在意料之中,只是什么时候获奖不是很确定。
从科斯、诺斯到威廉姆森,诺贝尔经济学奖三次选择了制度经济学派。这些年来在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比较突出的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除了科斯之外,还涌现出很多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做出的贡献非常大。
此外,制度经济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作为一种分析现实问题的工具,能够解释现实问题,并且提供一些解决方案。相对于经济学的其他学派,大家认为它更有解释力。
南方周末:这些年来,由于数学模型用得不多,制度经济学似乎并不在经济学的游戏场中心,不那么主流,所以也有西方学者对威廉姆森获奖感到失望。
盛洪:制度学派是不那么主流,但是不能这样评价——他用的数学模型不太多,他就不够成功。
恰恰相反,所谓主流经济学用了过多的数学模型,其实有利有弊。好的一面是显得特别精致,但是坏的一面随之而来——为了数学的分析,它舍弃了很多的现 实要素,做了太多的假定,应该说离现实更远,数学模型对现实的解释力反而更差。另外,人们太偏重数学解释,太偏重定量的分析,更注意局部和技术的细节,反 而不能从整体来看待整个社会,使得经济学看起来特别沉闷,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批评。
其实非主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它可以在主流的旁边有一些变异,有一些创新,反而能够获得发展的机会,而主流已经非常成熟、非常精致了,再往前去创新,难度就非常大。
新制度经济学其实也在不断靠近主流,原来制度学派特别非主流,现在它在尽量用主流的语言来表达它的主张、它的思想。这个非常独特的定位给它带来了成功。
南方周末:这30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理论。威廉姆森是这个学派的开创者之一,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他的思想?能不能谈一谈您对他的了解?
盛洪:威廉姆森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影响最早的一个人。他早在1987年就来到中国,在社科院工经所举办了一个系列讲座。第二年,威廉姆森又来了一 次中国,在体改所举办讲座。当时年中国改革开放时间不长,威廉姆斯能来中国很不简单。1986/87年左右大家刚刚知道有一个科斯,他的《企业的性质》在 1987年刚刚翻译成中文。威廉姆森的前后两次的讲座我都听了,听众很多。
他的讲座,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组概念和一个严谨的逻辑体系。比如他的核心概念是交易费用,用来解释各种经济制度,使人觉得从市场到科层组织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连续的制度谱系。后来他把自己的经济学叫交易费用经济学。当时感觉他特别严谨,对现实问题很有解释力。
在讲座中,威廉姆森推荐了自己的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我后来组织过两次翻译但是全部失败了——他的文字非常晦涩,看起来非常困难。
威廉姆森的特点是严谨、下工夫。他与科斯不一样,科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开创性的人物,而威廉姆森在获得了科斯的灵感后,把这种灵感深入下去,不断细化,用它来解释一些具体的问题,这是他的特点。他在画工笔画,很下工夫。
科斯的语言是非常平实的,很好读,诺思的语言比科斯更好读,而威廉姆森的语言实在是太晦涩了,如果他的语言再平实易懂一些,可能会更早获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就您而言,威廉姆森对您最大的影响,或者说他的学术对中国的意义在哪里?
盛洪:威廉姆森分析具体的制度安排。此制度非彼制度,不是一般讲的非常大而化之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之类,是system;他讲的是 institutions,中文可以翻译成"机构、机制、制度、组织"等等,是很微观的东西。他的这套东西,可以就具体制度的安排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制 度安排哪些地方值得肯定,哪里有问题,然后可以根据这些提出制度方案的改进建议。
比如说,一家企业需要很多的零部件,企业要做一个决定,是在市场中购买零部件,还是在自己的企业内生产?一个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有董事会?董事会由什么样的人构成比较好?
这些都是现实经济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威廉姆森的分析是一种细致的分析,比较实用,这对中国尤为重要。我当年的博士论文就用到他的理论和方法。
南方周末:获奖后,威廉姆森表示,获奖是件好事,可以帮助大家更关注制度经济学。这里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制度经济学还有许多继续要做的事情?
盛洪:要做的事非常之多。威廉姆森相信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个人很聪明或是很天才,但是他毕竟理性有限,寿命也是有限的,他能做的事还是有限的。可以说科斯、诺思和威廉姆森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反过来也可以看到他们没做的事更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这些年我们已经意识到已有的制度经济学理论相当粗糙。这些年我们在天则研究所不仅做学术,还给许多机构提供大量制度方案的建议,接触很多现实的东 西。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觉,如同那句老话,"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理论是灰色的",现实非常丰富,而理论相当粗糙,很多方面都没有涉及,要发展的空间应该非 常之大。为什么?从科斯到威廉姆森,他们都是学院派的,接触的现实还是比较少——虽然科斯特别重视事实,但是他们还是在学院里面,很多问题、很多事物的维 度都没有观察到。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到现在为止,新制度经济学更侧重有形制度的研究,还有非常大一块的无形制度,如道德、宗教、文化等等这些东西还没有被充分地纳入视野。诺斯后来就涉及到对意识形态、文化、知识等等的研究。要走的路还很长。
南方周末:中国这些年的变化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现实,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一天在中国出现科斯或威廉姆森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师?
盛洪:应该是没有问题,中国人很聪明,一点都不输其他国家的人。我们现在比较有利的条件,就是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制度变迁,这是中国经济学家优于其他 国家经济学家的地方。我们看这个制度变化发生,就在眼前,就如同亲眼看着猿是怎么变成人的。达尔文只是在猜,而我们是在亲眼看;这些美国经济学家实际上也 是在猜,诺斯讲经济史,也是猜的,但是我们在看,这是我们的优势。中国人都很聪明,所能掌握和获得的思维材料如此众多,应该有潜力。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有很多问题,因为前些年的封闭,我们的基础打得不牢,各种积累还不够。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大家又非常地匆忙,甚至有一些浮 躁,中国的学术氛围还没有达到美国那样,大家可以非常从容地思考理论问题——现在教授们还在整天忙着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同时做十个项目,其实不能静下心 来思考基本的问题。
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将来会有所成就,这一点我坚信不移。
南方周末:时间有多远?比如,20年、30年?
盛洪: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时间之内是绝无问题的。
南方周末:您是一位乐观主义者。最后,这次诺奖的主题词似乎是"治理",这是否意味着,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的价值钟摆从对市场和效率的高度关注往回摆了?
盛洪:或许还不能这么说。事实上,作为一个学派,新制度经济学还是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还是强调更多地用市场方法来解决问题,科斯定理就是这样的含义。而且并不是只有制度是约束,实际上市场也是有约束的,市场就是由一组制度组成的。不是钟摆往这边摆的问题。
但有一点很有意义,就在于金融危机的问题是什么?制度经济学家回答是制度问题,危机出现实际上制度是有问题。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政府有问题或是市场有问题——这个概念太大、太粗糙了,不能解决问题——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分析问题。
比如说金融市场上出的问题,不是要全面否定金融市场,而是要看金融市场哪些制度出了问题,可能是导致市场失灵,我们就要避免它,就在这个时候加强管 制。我们也要分析政府在哪些具体方面有失误,需要改进。可能这样一种更细致的分析,可以为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提供更好的制度解决方案,这是有意义的。
如果这样一个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家用所谓宏观扩张政策把它扛过去了,其实没有解决问题。真正要面对金融危机,还是要找到它的制度问题,提出新的制度解决方案。
本文删节版发表在《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