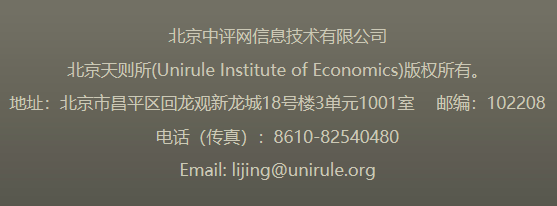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问题及其应对
康永久 吴开华
华东师范大学 广东教育学院
[提 要]在现行的多元办学体制中,存在着政府越权与卸责、制度性歧视、地方保护主义、对多元化的强制与限制及“地下产业化”等诸多问题。其核心是政府的教育管制无处不在,结果造成了新的条块分割,不同系列的学校之间彼此不沟通,“教育货币”(在此指主要教育权利、国民资格、政策优惠等)不能在它们之间自由兑付。要走出当前的办学困境,必须以超前的眼光、务实的心态,超越围绕教育服务性质问题而展开的意识形态论争,以市场化的思路克服现有多元办学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在努力追求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同时把握市场化、产业化的大局。而教育券计划就是这样一种通过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打破国家对教育的行政垄断,促进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确保国民教育权,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的制度设计。
[关键词]多元办学体制;教育管制;教育服务;教育产业;教育券;国民教育权;统一教育市场
Multi-System for Running Schools: Problems and Answers
Kang Yongjiu Wu Kaihua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dong Teachers College
Abstract: There are quite a few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Multi-System for Running Schools, such as the control and buckpassing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institutionalized discrimination, the regional protectionism, the coercion and limit to the pluralization, and the “undergrou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kernel among them is the omnipresent control from the government. As a result of it, new Vertical-Horizontal Separations in education have been caused, schools belonging to different systems can not communicate one another, and the “educational currency”(such as rights of education, the qualification of citizens, favorable policies, and so on) can’t be freely “cashed” among them. If wanting to overcome the predicaments in the Multi-System, we must, with foresights and realistic attitude, transcend the ideological disputes on the natures of educational service, impel the educational market ulteriorly to overcome the i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in the present Multi-Systems for Running Schools, grasp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plural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Voucher Project is just an institutional design through which we can create a unitive educational market to break the administrative monopoly of the educa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accelerate the fair competitions among schools, and insure the civil rights of education, entirely improve the qualities and benefits of education.
Keywords: the Multi-System for Running Schools; control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service; Indust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Voucher; civil rights of education; unitive educational market
一、“多元办学体制”的界定
(一)多元办学的现实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政府与学校关系问题上,如何形成一个既利于政府进行统筹管理,又利于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学校还有较大的办学自主权的办学格局,成了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办学体制改革,进一步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状况,形成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相结合的新体制。我国多元化的办学格局由此逐步形成。
(二)多元办学体制的界定
理解多元办学体制,关键在于对“办”的理解。“办”有时指的是“举办”、“创办”,强调的是办学经费的来源,如“投资办学”、“捐资办学”中的“办”即为此意。“办”还可理解为“经营管理”的意思,“办学者”、“办学理念”中的“办”即为此意。如此,不同的举办主体(主要经费来源)和不同的经营管理机制相结合便构成不同的办学形式,不同办学形式的体系和制度便成为办学体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多元办学体制作如下粗略的区分:
经营管理形式
公营或国营 民营/私营
主要经费来源 国有资产 公办/公立学校 公立民营学校
非国有资产 私立公营学校 民办/私立学校
就我国办学现状而言,办学形式主要是上面所说的公办学校、公立民营学校(亦称为国有民办学校,包括公立转制学校)和民办学校三类。私立公营学校在理论上存在,在实践中有争议。有些人称私人捐建而公家接管的学校为“私立公营学校”,但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倒是私营企业在建国初期的国有化改造过程中出现过短暂的私有国营现象,但现在也不复存在。
现在让我们对现有的三类学校做一些说明。
1.公办学校
完全意义上的“公办”学校,其举办主体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经费来源为国家财政性拨款,经营主体是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代理机构或人员。国家或其代表(“各级政府”)完全拥有学校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等各项产权,同时享有由此派生出来的管理权限。非完全意义上的公办学校则包括由国家或其各级代理控股、并由国家公派人员控制着学校运作的股份制学校。这类股份制学校在理论上存在,在实践中则很少见。但无论如何都可以说,国家或其各级代理(政府)在经费资助和经营管理上的主导地位,是区分公办学校和其他类型学校的根本标准。
2.民办学校
“民办学校”是指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称非政府组织,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利用自筹资金,经主管机关批准登记注册的面向社会举办且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运行的正规教育机构,既包括个人或非政府机构独资的私立/民办学校,也包括个人或非政府团体按股份制形式组织起来而创办的股份制学校,甚至包括政府参股但不控股的股份制学校。
在我国,近几年来,“名校办民校”,成为教育发展的一种值得注意的类型,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最近在我国南方地区掀起的“新一轮民办教育冲击波”。它是一种公立名牌学校利用自己的品牌,自己筹集资金或与公司合作办学,从而扩大公立名校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办学形式。
名校进军民办教育市场,由于其名牌效应而能吸引社会雄厚的资金,这在广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广州的名校办民校,第一是坚持在新学校的校名上打上名校自己的名称,如华师(华南师范大学)附中番禺学校、南海执信中学等,旨在显现对质量的要求及对社会的承诺。第二是民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有相当一部分由校本部派出,而新学校的新教师则首先要到本部任教一年半载,以充分感受本部良好的学校氛围。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即名校在与办学合作者洽谈合作时的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学校要按21世纪的要求来建设,要成为21世纪基础教育的楷模,有超前意识;二是在合作过程中不要干扰学校的办学,要真正做到教育家办学,教育家治校,学校拥有完全的办学自主权;三是要在服务社会上达成共识,不以营利为目的,不能急功近利,从而保证学校的教育质量。
但这类学校的准确定位,实在要因校而异。因为这类名校本身是公立/公办学校,其无形资产应属公有资产。在办学过程中还涉及到调用公办教师,并借用其他公共教育资源。在经营管理形式上,也是公办学校起主导作用(需要承认的是,这是公办学校中的自发力量在起作用)。因此,相当一部分这类的“民校”——尤其那些占用了太多公办学校资源、以致流失到这类学校中的公有资产占据了学校资产的大部分的学校——应归属到下一类“公立民营学校”的范畴。
3.公立民营学校
也可称“国有民办学校”。它的开办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或政府,但在经营管理上采取的是“民营”方式。在学校的后续发展经费上,这类学校存在一定的变数。但如果要继续保持其“公立民营”的性质,必须确保公共办学经费的主导地位。
有人称这类学校为“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学校。在国家的正式文献中,也有过“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表述,如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1月14日颁发的《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中就肯定了“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形式。但从法律上讲,“民办公助”或“公办民助”中“助”,应理解为“捐助”,实质属于捐赠性质,不是投资,故捐助人在将财产捐出之后,不再享有对财产的所有权。但也有人认为“助”乃帮助、辅助之意。不过,即便如此,只要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不能改变学校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讲,“公办民助”学校就是公办学校,“民办公助”学校就是民办学校,将“公立民营”(国有民办)学校称为“公办民助”、“民办公助”是不恰当的。
公立民营学校在我国还有一个使用频率相当高的称谓,即“转制学校”。学者们关于转制学校的界定探讨,更多的是关注“转制”中的“制”究竟指什么。是“所有制”、“体制”、“投资体制”、“管理体制”,还是“运行机制”、“管理机制”?一种主导性的意见认为,“转制”的理想结果是实现三个转变:第一,在教育资源国有制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教育资源的重组,转变投资体制,使原来单一的政府教育财政投资转变为政府和社会多渠道投资;第二,转变管理体制,从政府原来直接的指令性的行政管理,转变为一种宏观的、指导性的调控管理;第三,运行机制转换,学校在内部的管理上,在经费的使用上,在教育教学的组织上,在人事分配上,拥有比较大的自主权。 也有学者认为:转制学校改革的出发点应该是建立合理的学校产权制度,具体可以有三种选择:政府授权组建“教育经营公司”,收购一部分“转制”学校成立“教育集团”,由“政府经营”向“公司治理”转变;引进其他办学主体,实现学校资产多元化、产权结构多元化,改变学校组织架构,政府应果断退出办学领域;实施学校产权交易,对部分转制学校进行资产置换,转变办学主体,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私立或民办学校。
归纳上海转制学校近十年发展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对我们界定“转制学校”会有帮助。上海的转制学校主要有以下突出的特征:
(a)转制学校主要来自公建配套学校、薄弱学校、撤消建制学校等“边缘性”、“末位”性的公办学校。
(b)转制过程通常受到政府支持,主要表现为提供校舍、推选校长、保留教师编制、提供开办经费、放宽招生计划,等等。
(c)转制后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包括按成本收取学费、争取赞助、规范管理、减员增效、按劳分配、改革课程、教学创新、提升质量、面对市场。
(d)转制三年后,完全自筹经费办学,逐渐积累发展资金,投入学校建设发展,甚至向政府缴纳校舍租金。
基于上述特征,可以说:转制学校是一种由国家提供校舍、教师编制和开办经费,由家长承担教育教学成本,由校长和董事会承办,实行效率优先、资源多元的混合型学校。
由此可见,所转“制”的同异(因为所转之“制”,有学校产权所有制与学校经营管理制度之分)、“转”的程度的差别,都影响到“转制学校”的具体定位。由于“转制”是个过程概念,它不足以表示这类学校的确切性质。只有那种只改变学校经营管理方式,未根本变革学校所有制结构的公立转制学校,才可以称之为公立民营学校。但实际中的转制学校很多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当然,就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转制学校”或“公立转制学校”,作为公立学校转制现象的描述词并无不可。
需要声明的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是中小学教育阶段中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问题及其应对,对办学体制的界定和研究主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但在某些地方也涉及了学制系统的其他方面。
(三)本课题国内的研究现状
当前,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构成为了人们研究的焦点。一是深化多元办学体制的可行性、合法性问题,如可不可以营利的问题、所获收益可不可以分配的问题、究竟该选择哪些学校(重点学校还是薄弱学校)进行改制的问题;二是如何引导规范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堵塞现有多元办学体制的制度漏洞以实现合法化的问题;三是国外办学体制及相关教育制度改革的思路与现状的介绍与借鉴问题。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人们在第一个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论争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多元办学体制的引导和规范也只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现有多元办学体制自身的先天不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突破现有多元办学体制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办学体制弊端的研究始终没有能够出现,以致理论研究并没有充分发挥引导实践建设的功能。而在对待国外办学体制与思路方面,人们直到目前主要还只处于观望阶段,在其可行性上通常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鲜见有实质性的研究和尝试。各方的教育意愿或者在研究中没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就是在研究中被误导或误读,“让事实说话”在其中实际上没有多少说话的余地。
二、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问题及其根源
多元化的价值理念和办学思路,如今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认同,再在这一问题上纠缠已没有什么必要。实际上,如果真正是多元化的改革,反对这种改革的一方仍可以在这种改革环境中得到必要的尊重和保护。因此,停止这方面的争论其实也无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问题是,当前的多元办学体制与政府高度集权的旧有体制之间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此衍生出各种复杂的办学困境,继续困扰办学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政府对教育改革事务采取过度干预立场,则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它不但导致政府本身的自我卸责,而且导致政府不能对现有的多元办学体制给与同等程度的认可(制度性歧视)。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在便于政府管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与制度性歧视一道造成了多元办学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局面。此外,政府的教育管制还导致了对多元化的强制与限制。地下产业化则是政府管制框架下的多元办学体制必然存在的第二副面孔。下面就让我们对这些问题按其内在逻辑关联由里及表进一步加以剖析:
(一)政府的越权与卸责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政府的越权行政或过度干预问题。出于传统、习惯和利益考虑,政府部门(包括教育主管部门和归口管理部门)至今仍然偏好以直接、具体、微观的手段来行使职权,导致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不适当地干预公办学校事务,甚至不惜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越权行政。而作为多元办学体制中的一元的公办学校,则是政府教育管制的重灾区。它们在简政放权的国家体制改革中办学自主权虽也有了增加,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被称为计划体制的“孤岛”或“最后的堡垒”。可以肯定,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可以带来局部的教育繁荣,但绝不会带来普遍的教育繁荣。
我们在广州市番禺区进行教育调研时发现:
1.教育局有自己下属的教育发展公司,控制着教材、教辅资料的征订和校服的定做。今年9月,广州市番禺区将成为新课程的改革试验区,都将使用新教材。为此,教育局统一规定:学校通过新华书店自己征订的材料统统不能用,只有由教育局盖章审定的材料才准使用。
2.当地有几所学校正在申报省一级,全校的教学秩序大受冲击。教师们被安排彻夜加班加点做资料(学校的各项工作都有档案方面的要求),学生则忙于接受日常行为规范的训练并应付学校的环境卫生检查评比,家长则被安排接受配合学校申报工作的各项指令。上面不断有领导下来,提醒学校做事要慎重,防止检查组刚一进校就接到家长或教师的投诉电话。会议则一个接一个,不断为即将到来的评估筹划着。整个学校工作都被申报评估搅乱了。
3.教育督导工作之细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所见到的《广东省(市、区)推进教育现代化督导评估指标体系》、《广东省中小学等级评估指标体系》以及番禺区《小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和素质评价表》都极其繁琐。以对学生个体的评价为例,该体系分5大类28个小类,每小类又都有4个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又都有具体的分值标准,每一分值标准又都有具体的评分细则。班主任每学期都要按要求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统计评定。值得注意的是,对教师也有类似的个体评价方案。
4.我们在下面一些学校进行教育改革试验,但总发现学校工作与我们所推进的改革工作是两张皮。有学校和教师提出:我们倡导的教改和科研要照顾到学校的实际。但学校的实际又是什么呢?除了很多学校对自身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之外,来自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归口管理部门的检查评比也是“烦恼”之源。主要是竞赛多、检查多、活动多、突击任务多和文牍主义盛行,尤其是政工线上的罗嗦事多,重复统计报表多。而且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投资者、办学者、管理者与学校教职工各方的责、权、利关系难以理顺。
5.在强行政介入的办学体制下,首长工程和面子工程以及相应的造假工程是不可避免的。当地的学校有省一级,也有不达标的。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所谓的窗口学校,是给人看的。既给外面的人看,也给自己的领导看。办学经费的拨放很多时候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其中也包括借助各种教育督导来向办学部门伸手。那些薄弱学校的校长则被认为“不主动”。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也为了打开领导的钱柜,学校往往动用各种虚假信息,包括他们自己所说的“哭穷”。
这种过度干预的危机在公立转制学校仍然没有得到根除。公立学校转制以后,作为董事会中的多数和校长任命机构,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行政控制轻而易举,指令性行政管理仍大行其道。其它新兴的民间办学机构,现在也仍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而不能按照市场模式运作。以私立/民办学校的办学为例,由于高考指挥棒的影响,私立/民办学校比公办学校更看重学生的升学考试成绩,这被当成私立/民办学校的生命线。因此,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能摆脱应试教育体制束缚的贵族学校(它们实际上只是一种留学预备学校,学生的大部分将被送往国外)之外,绝大多数的私立/民办学校都在实行一种比公办学校更为传统的应试教育模式。只要政府不把对教育的过度干预改为依市场机制的管理,这种局面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克服,私立/民办学校的体制优势就只能转化为一种更为坚决地贯彻应试教育的体制优势。实际上,在占绝大多数的公立学校仍然按照计划体制的模式运转的制度条件下,期望少数私立/民办学校能按现代教育的理念自主运转也是不切实际的事情。
过度干预或管制的另一面必然是卸责或放任。放任一方面是自我放任,另一方面是对管理对象的放任。由于政府管了许多本不该管的工作,而且对这些工作管得过多过死,以致很多时候根本就忽视了自己的本职,甚至想都没有想到自己还有什么别的“本职”。这种自我放任首先就表现为政府在义务教育发展中的自我卸责。由于政府在教育战线全线投资,本就不足的教育投入更难发挥应有作用,结果造成公共投资主体因开支庞大而无力支撑,宏观社会效益又非常低微,家庭个人投资能力充裕却因可免费“搭便车”坐享教育收益而无投资积极性的博弈困境。这样一来,本该由政府管理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政府却无力应付,而是下放给地方和各个微观办学主体,任由它们“多渠道”筹资办学。此外,作为教育中的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尤其是作为正式教育制度的唯一供给者的政府,在这一方面工作也严重滞后。从一定意义上讲,多元办学的混乱局面,正是由于政府未能担负起制度创新的责任造成的。
我们翻遍了广东省近几年的教育政策法规,发现教育主管部门仍然停留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境地,缺少对自身清晰而又清醒的定位。
许多文件是应景之作,如关于表彰南粤优秀校长、南粤杰出或优秀教师的通知、关于开展保护环境创建美丽校园活动的通知、关于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的通知、关于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通知、关于开展尊师重教活动的通知、关于表彰尊师重教先进单位的意见等。
更多文件是应急之作,如关于严禁学校更改公民民族身份的通知、关于学校内有关气功问题的通知、关于收取储备金的民办学校改收学杂费问题的通知、关于做好“收支两条线”工作的通知、关于学杂费减免和困难补助的通知、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内学生用品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预防学生食物中毒工作的通知、关于中等专业学校教育资源流失的意见、关于加强对教育网站和网校管理的通知、关于中小学德育基地收费问题的通知、关于中小学校不准代办学生保险的通知、关于严禁以共建招生的名义向学生违规收费的通知、关于加强学校安全与消防工作的通知等。
还有许多文件是夹杂不清的越位之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工作,定了许多不该定的指标。那些高瞻远瞩、定位清晰的开拓创新之作是少之又少。
而政府教育管理中对管理对象的放任则主要表现在政令不畅方面。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种情况则是政府不恰当的决策导致其自身难以付诸实施。当然,很多时候是这两种情况的混合物。以教育减负问题为例,建国以来有关教育减负的文件出了不少,群众运动也搞过多次,但每次都如泥牛入海,而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又确实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症结究竟在哪里呢?在我们片面、想当然地理解了学生的负担,而没有把对负担的界定权真正交给学生,交给市场。实际上,教育管理中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现象很多时候都说明一个问题:政府部门对自己的政令没有深思熟虑就推了出来,但下达一个不完全适合的政令又该如何收场呢?强行推行只能招来更大的损失,因而很多时候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时候甚至只能通过上下勾结蒙混过关。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卸责问题,与政府的自我卸责都很有关系。
(二)制度性歧视问题
多元办学体制中的制度性歧视首先存在于公立学校与私立/民办学校之间。到目前为止,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很多时候仍只是公立学校的主管部门,只愿对公立学校负保护、支持责任。在它们眼中,公立学校是“亲生”,入“正册”,私立/民办学校是“野生”,入“另册”。在公民办/公私立学校竞争中,它们不是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而是站在公立学校一边。招生时,首先满足公立学校在生源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需求,对私立/民办学校则采取限制措施,有时甚至根本就禁止私立/民办学校的介入。许多私立/民办学校的校长不无慨叹:同样是校长,但遭遇不一样,当公立学校校长时处处受尊重,自从当了私立/民办学校校长,处处求人,看人脸色,连一般的小职员都可以随便训斥。
带有公立性质的国有民办学校和纯粹的私立/民办学校乃至普通的公立学校之间的制度性歧视则更为显著。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发展这些学校,允许他们以优惠条件提前招生,这就使他们在保留名牌学校名气的同时,既能拥有私立/民办学校不划片招生的优势,把周边地方的“尖子”学生先招到学校,又能拥有普通公立学校所不能企及的自主权利。一位公立民营学校的校长由衷地说:“在整个办学过程中,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是办不起来的。”有了这么多有利条件,转制学校的迅速崛起就毫不奇怪。有这么一两所不在体制内而又享受着体制内都很难享受的特殊待遇的“翻牌”学校,就很容易垄断当地优质的教育资源,造成极度的不平等。对于这样的结果,人们不得不困惑:在办学体制改革中,政府的职责到底是什么?教育事业的公益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公办学校的校长特别羡慕那些有着体制性优势的转制学校,以及那些有着官方背景的公立民营或公办民助学校。以深圳的北大附中为例,它是北大、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创办的一所带贵族性质的学校,学校的物质条件是一流的,由政府无偿提供的地皮是一般学校的6倍还有余。它的理念也最先进,是北大的“民主科学、兼容并取”,而且学校工作基本不受督导评估工作的干扰和限制,因为其不属于受国家管制的公立学校之列。在公立学校中司空见惯的为应付上级检查和评比而连夜造假的事,在那里根本就见不到。在课程的设置上,有专门的特长课和国际理解课,特别注重校本课程的开发,音乐课和美术课也是两节连着上,一开始就注重给学生专业化的训练。在广州的调查中,有名校的校长也告诉我们:最希望国家能帮助解决名校所办民校的场地校舍和教师的编制职称问题,其他的(包括教师工资)由学校自行解决,政府不妄加干预。
从现状来看,民办教育/民办学校处于配角的地位,并在学生升学就业、教师待遇等许多方面受到歧视,是制约和束缚民办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实际上,民办教育一直都能明显感受到来自公办学校的强大压力。而现在这种压力由于国家对1000所大规模的示范性、寄宿制高中的大力扶持而进一步增加了。可以说,少数带有特权性质的公立学校(包括公立民办的学校和重点公办学校)在借助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力量挤压私立/民办学校(乃至普通公立学校)的生存空间。现在看来,私立/民办学校中普遍存在的教师积极性不高、教学效率低下、教育教学理念极度落后的局面(这方面我们有对广东最著名的私立/民办学校的现场考察为依据,在那里我们发现他们的教育教学观念还停留在10年以前的水平,仿佛与当前轰轰烈烈的教育教学改革隔绝一般),也要从对民办教育的制度性歧视中寻找答案。
《民办教育促进法》似乎给了私立/民办学校一线生机。它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第五条)“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第二十七条)为体现这一原则,该法还规定:“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权利。”(第三十一条)“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先进评选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权利。”但要真正在实践中消除对民办教育的制度性歧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民办教育促进法》(草案)在2002年10月28日的九届人大第30次会议上第三次提请审议时未付表决,原因是“在几个重要问题上意见分歧,一时难以提出修改方案,需要进一步研究”。草案再次重申:民办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应当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同时也提出:“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和国家有关规定必须提取的费用以后,举办者可以取得合理回报。”正是这一有关“合理回报”的规定引发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反对的意见主要有八个方面:(1)合理回报本质上是营利,违背了教育法第25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定;(2)发展教育事业应主要靠税收优惠,而不是靠合理回报,合理回报不符合国家需要,也不能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3)想要赚钱的民办学校没有一个肯到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去办学,这与国家促进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宗旨不符;(4)举办教育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义举,规定取得合理回报是对这种义举的玷污,民办教育因此也不能健康发展;(5)对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主要以精神上而不是通过合理回报给予奖励和鼓励,即便要从物质上进行回报也应用物质“奖励”代替“自取”;(6)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教育机构混在一起,会导致税收政策的混乱,如果硬要回报就不得给予公办学校同等的优惠条件;(7)从国外的情况看,凡是营利性的学校都没有什么前途;(8)所谓“合理回报”不是合适的法律术语,缺乏确切的含义,其方式和数额在法律中都很难做出规定。
制度性歧视在不同等级、不同性质、不同体制的公立学校之间也广泛存在。有几种经常发生在公立学校体系内部的等级区分,确实值得我们关注。 当前处于舆论焦点的是重点公立学校和非重点公立学校之间的制度性歧视问题。由于这种歧视,许多严重的教育问题出现了:一是教育资源的这种定向分配方式降低了资源的使用效率并造成教育中的特权意识。二是这种重点中学体制导致重点中学成了应试教育的主力军,办学特色不突出,只能是让学生求同存异,也降低了本应能达到的教育公平竞争程度。三是在外部制度框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现实情况下,重点中学日渐成了少数人(包括特权拥有者)的牟利工具或后花园,因而即便是重点中学在人才培养问题上的高效率,也开始不为人们所认同。
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的等级区分常常也是这样一种等级区分。对个人而言,这种双轨体制增加了人们在不同轨道的学校之间往返的难度。对教育而言,它阻隔了教育与现实生活相沟通的道路,同时也断绝了不同教育之间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可能。对社会而言,这种双轨体制限制了可供选择的后备人才的范围,同时也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摩擦成本。它曾经乃至现在的实际存在,只能说明两件事情:一是它具有某种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效率特征,这是它得以存在的直接基础;二是它为某些人提供了一些潜在的收益,从而间接支撑着它的运行。随着知识和技术更新步伐的加快,现代知识和高新技术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愈发突出,以及人们文化教育方面需求的日益增长和频繁变动,以实用工艺技术的传授为基础的职业学校和以普通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为基础的普通学校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在我们国家也一直存在。1982年我国对重点中学的一次调查显示,在13个省、市、自治区的348所重点中学中,城市243所,占70%,县镇98所,占28%,农村7所,占2%。 这种教育中的城乡二元体制在国家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抛开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向城市的过度倾斜这种人为的社会不公不说,这种教育中的城乡二元体制也存在着效率上的深刻缺陷。农村学校中的低效率自不待言——由于受困于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长期以来,农村学校处于超负荷运转的艰难境地和粗制滥造的教育层次。城市学校的效率因此也成问题,长期处于一种得过且过和等要靠的状态,并降低了城市学校教育影响的辐射力。而且,这种教育体制与其它社会体制一道,限制了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造成了一种新的身份的等级制。
值得注意的是,现今教育方面的制度性歧视是一种双向歧视,既有对私立/民办学校的正向歧视,也有对公立学校的反向歧视。其中对私立/民办学校的歧视是显性歧视,是直观的、为人所熟知的。对公立学校的歧视是隐性歧视,至今尚未为人们所重视,但确实又是存在的。如有关公立学校不得择校、择校须到私立学校或国有民营/公立民办学校的规定,名义上是保护公立学校的主体地位,实际上是削弱这种主体地位,而且这种削弱是暗中强制进行的。由于不能接受学生择校,大量的择校资金被引向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宝贵的自我发展的机会,也丧失了发展特色或个性化教育的机会。在可预期的教育市场化的浪潮中,公立学校已经晚走了几大步。以“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为口号的社会改革在教育领域没能破除对教育系统的制度性分割,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三)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教育中的地区性分割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着。户籍管理制度对个人教育选择的限制既是导致教育活力不足的一个因素,也是导致个人教育选择成本无限度地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以往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感召下,教育中的地区性分割主要还只表现为城市和农村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改观,反而有不断增强的趋势。由于加大了地方在教育发展中的权责利且因此而降低了教育责任主体的重心——基础教育的办学权被首先下放至省并最终下放至县,各地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割据局面,教育带有了更强烈的地方色彩。结果,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继续盛行并蔓延开来。
这种地方保护主义首先表现为入学中的地方教育壁垒的出现。今天,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已经成了影响国计民生和社会安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尽管在政策上允许借读,并且也设置了借读费方面的限制,但由于缺少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各地也缺乏执行这一政策的足够动机(反而有暗地鼓励辖内学校高额收取借读费以解决地方教育经费不足问题的激励),公立学校在“解决”借读问题时又缺乏私立学校的有效竞争,结果,借读费高居不下,实际上演化为“择校”,与面向私立学校的择校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公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根本得不到承认。
更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是,国家对地方教育利益本身也进行了条块分割,这些条块分割在历经世事变迁之后,造成了各地考生在高考中的不同处境。有的省份(或直辖市)本身拥有较多的高等教育资源,或者在国家的高校布局中居于有利地位,并且通过各种共建或资助活动获得了高校在办学上对它们的依赖性,因而取得一种在学位分配上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在国内教育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有些省份则凭借某些倾斜政策获得了一种相对优势。这样一来,不同地区在高考录取分数线上出现显著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维持或消除这种地方差异,各地从民间到政府,都展开了各种寻租活动和策略行为。这些地区分割和相关的策略行为对基础教育(乃至当前的义务教育)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近年来,外省考生通过非正常方式大量涌入海南参加高考的趋势愈演愈烈。为何要南下高考呢?原因很简单,海南基础教育相对落后,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内地省份,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就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再加上海南建省后,上至教育部、下至全国各高校,每年都向海南拨出充足的招生名额,海南考生录取比例往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许多考生没有在海南上学,却把户口迁来海南参加考试,从而出现“高考移民”。随着“移民”的增多,海南本岛的学生和家长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愤慨,由此引发的争议和冲突不断,引起海南有关部门的关注。在日前召开的海南省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王琼瑾等11名代表向大会提交议案:抓紧完善、尽快出台《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报名条件暂行规定》,呼吁以法规的方式规范高考报名,以法治“考”。王琼瑾说,以“法”治考可能会触及少数人的利益,但保护了大多数人的权益。北京、上海等市也有限制外地考生报名参加高考的规定,海南应尽早落实完善有关措施。
就近入学的教育政策,不但给予了地方在教育中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合法性,而且使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在同一行政区划内的不同学区之间也都蔓延了开来,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条块分割。名义上,就近入学体制保护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确保教育公平。在实际工作中,就近入学体制确实也导致了教育中的平等浪潮的重新崛起。前几年的薄弱学校改造运动和最近几年兴起的学校均衡化发展运动均是如此。但重点学校和其他特权学校还是可以摆脱与这种办学条件标准化相伴随的平等压力,提前实现办学条件的超标准化。因此,就其实效而言,就近入学体制保护了少数人对优质教育资源、优质教育服务长期的低成本占有。
今天,我们可以更加真切地看到,就近入学体制并没有像它所宣称的那样为人们提供一种更加公平的教育。不但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在拉大,学区之间的教育差距都有不断被拉大的趋势。而当社会上提出开放教育市场的要求时,最先站出来反对的,就是那些在现有的条块分割的招生/就学市场中占据有利位置的人和组织。他们不愿开放自己的教育市场,提出了从公平一直到效率的各种理由,丝毫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体制对至关重要的国家认同的伤害。而且,就就近入学政策的教育意义而言,有一种真正的限制即便特权学校也难以幸免,那就是对特色教育的限制。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要在不同学区、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省市之间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壁垒,就必须优先考虑教育的同质化问题,即必须首先将各地的学校统一办成大而全的无特色模式,只有这样才能抑制住人们对特色教育的“索购”倾向。由就近入学导致的这种优质教育资源向权力中心集中的现象妨碍了优质教育、特色教育的发展,最多通过政策倾斜形成某种基于特权的特色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是以金钱择校作为补充的。从根本上说,它并不限制择校,但它限制贫困学生择校,并使之永远贫困。原来蕴涵于择校中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就是认为它是富人的游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金钱为依托的择校是以“劫富济贫”为特色的,或者说,是带有了几分“劫富济贫”色彩的。但实际情况是,先富起来者的子女被不适当地剥夺了教育上的平等权利,未富起来者的子女却并未得到实际的好处,而且更加严重的是,他们及其子女对择校的需要被严重地遏制了。可以说,就近入学中体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对后者的约束远远大于前者。因为前者有超越这种约束的经济实力,后者没有。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后者的择校需求或愿望一点也不输于前者,这一点甚至可以放到消除贫困的高度来看待。看看今天珠江三角洲的私立/民办学校的规模,再看看这些学校中学生的家庭境遇,我们就可以知道择校对那些尚未富起来的家庭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父母的工作机会(因而也是超越的机会、脱贫的机会),意味着父母对子女和社会的关爱和责任,还意味着下一代的起点和视野。但我们又看看接纳这些孩子的学校教育质量的低劣,再看看我们的公立学校不断因招不到学生而关门和合并、从而导致至少在目前看来仍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流失的惨状,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的就近入学政策和就近入学赖以生存的地方保护主义立场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多大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据调查,现在沿海各地都有一些黑市学校或窝棚学校。这些学校办学条件低劣,往往租一层厂房就开始招生和招聘,生源主要是外地民工的子女,收费虽然比公立学校的学费要高,但低于公立学校的择校费和正规私立学校的学费,大致为一两千块钱一年。这些学校的淘汰率非常高,据估计,在深圳,每年有30%的私立学校消失,又有30%的私立学校兴起,其中主要是这一类学校。学校的高淘汰率对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伤害都非常大。这些学校的存在不仅彰显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影响着社会秩序,而且腐蚀着教育的机体——在每一所黑市学校的背后都有一个利益关系网,否则,这些学校是根本不可能有效存在的。家长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子女往这类虎口中间送呢?主要原因是小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比在这类粗制滥造的学校中更容易变坏,而公立学校由于就近入学的限制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入学的门槛很高,他们根本就无力承担高昂的择校费。
广州曾经发生过几起因民办学校办学条件不达标而被勒令停办的事件。这类事件最令人深思的是:教育主管部门为了维护学生或教育消费者的利益而开展的这项清查运动究竟是否达到了预定的目的?更深层的问题是:为什么学生及其家长会选择这类粗制滥造的学校?他们完全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上了坑蒙拐骗的当了吗?在我们看来,正是教育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造成了这种选择局面。特权教育体制排斥这类学生和家长,因为他们没有就近入学的权利。这就给非法办学留下了巨大的牟利空间。
目前教育中的广泛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妨碍了个人法定的受教育权的行使。本国国民在受教育上的国民待遇在这种体制下都得不到有效的保证。经济领域的社会化、工业化、都市化和市场化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教育的发展不是促进资源的合理流动,而是限制资源的流动,加剧教育中本已存在的条块分割。
(四)对多元化的强制与限制问题
政府对多元化的强制主要体现在对公立学校强行改制问题上。迄今为止的公立学校转制多半是在政府策动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改革的目标、进程和方向往往都取决于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而不是基于市场化的运作或平等参与的公共选择,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下列问题:(1)政校依然没有分离。对于转制学校来说,法人地位并没有真正确立。很多地区,董事会只是做做样子,有的地方干脆就不设,实际还是由政府在具体办学,并且将其纳入到公办学校系统内统一管理。(2)负盈不负亏。由于政校不分,学校责任主体实际上依旧是政府。学校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承包”或“租赁”的关系。学校盈了,皆大欢喜。若亏了,还得由政府“托盘”,学校本身并不承但责任。(3)短期行为严重。由于组织结构依然照搬公办学校的办法,校长并不是由董事会投票民主选举,而是政府选聘,因而校长不是直接对董事会负责,而是直接对政府负责,办学行为极容易短期化。最后,(4)教育资产容易流失。转制学校由于缺乏微观监督机制,也由于信息不完全,政府无力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学校资产并没有“人格化”,校产责任主体“缺位”,政府的监督成本非常高。
要知道,政府推行的公立学校转制改革,转掉的应是“困境”,是旧体制,是旧的观念和运行机制。然而,如果政府对转制学校撒手不管,甚至一卖了之,把卖学校当作官场一种权术来运作,转嫁危机,使转制学校或卖出去的学校重新陷入困境,那么势必影响教育的质量、改革的声誉和政府的信誉。
广东公办名校转制,尽管具体方案各式各样,名校转制后政府和老百姓得到的好处最多,但引发的争论也最多。因为一改制,学生们要么缴纳高额学费,要么“另谋低就”,转入普通学校。
几个穷人领着孩子挥泪告别名校,这个景象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成千上万孩子早已悄无声息地被排斥在名校校门之外,甚至排斥在普通学校校门之外。政府集中本已十分短缺的教育资金,供养一二所重点学校。百里挑一的精英,借助这副跳板考上大学。而无数无望升名校的孩子,在简陋的学校里混完义务教育的日子,或者干脆早早地放弃学业。这样的名校,又怎么称得上是“穷孩子的出路”,群众又哪里来的“教育权利公平”呢?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对民间自主办学的限制。我国对私立/民办学校的设置采取的是双重登记管理体制。一方面,私立/民办学校的举办必须首先获得有审批权的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而从广东的情况来看,批准与否的标准主要有三条:(1)私立/民办学校的设置是否根据当地的人口、教育资源、教育需求和学校的分布情况,且符合当地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2)是否能够提供完整的办学文件资料,包括办学申请书、办学可行性研究报告、选址报告和建筑设计平面图、学校章程、学校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学校招生范围、学校经费概算、校长及师资配备计划、教学及教材选用计划、办学经费来源及证明文件、主要举办者和管理者的资格证明文件、以及联合办学的联合办学协议等;(3)是否能达到办学登记的设置标准并符合国家规定的其他基本办学标准,这些办学标准包括场地、校舍、师资、设备设施、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我国,作为登记管理机关的民政部门同样对私立/民办学校的设立享有实质性审查的权利,即在取得审批机关颁发的办学许可证后,还需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到相应的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后,方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这实际上就给私立/民办学校的开办设置了双重障碍。这样,只要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有一方不同意,私立/民办学校就不能合法成立。有学者称其为登记管理制度上的“双重许可主义”。 这种登记管理制度不利于私立/民办学校的设立:它不仅使私立/民办学校的设立程序更加繁琐,而且由于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管理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在具体问题上极易发生分歧,给私立/民办学校的设立带来很大的不便。实际上,许多私立/民办学校在没有进入筹办程序时就已经被“扼杀”在襁褓之中了,而被“扼杀”的理由通常就是其不符合当地的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而那些即便能成功获准登记的私立/民办学校,在办学上也比一般的公办学校受到更多的文牍主义的限制。
在广州番禺的调查显示,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教育集团的介入非常不放心。在番禺的华景新城的建设过程中,开发商在自己的规划地段上配套兴建了自己的私立学校,以满足自己的住户和周边地区的客户子女的入学需求。但学校建好后教育主管部门觉得教育质量难以保证,一旦在办学的过程中出现什么麻烦会影响到地方的稳定,各种罗索事本身也会给教育主管部门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不允许他们自己办学,而是中途接管了这一学校,把它变成了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办学体制为公办民助,教师实行聘任制(校长和三个教学骨干是公办教师,上正轨后,三个公办教师要抽回),面向全国招聘。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市桥南郊的本地生源,不收择校费;另一部分为外地生源,现在办学才刚刚起步,也只收了借读费,没收高价,以后要收。在办学经费方面,现在不足的方面仍由政府补贴(总开支- 总收入= 政府补贴)。区政府希望今后能逐步减少投入,让学校自己养活自己。因此,对学校的要求是在短期内办出特色,打出名气,促使良性运作。当然“想是这么想,到时候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值得注意的还有对学校自主运作的限制。以择校为例,现在的择校制度只允许对私立学校的选择,不允许对公立学校的选择,并将对公立学校的选择行为限制在“借读”的范围之内。从实践的情况来看,私立学校由于减少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择校生招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优势。而公立学校则丧失了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得发展契机的合法性。此外,在收费问题上,由于对乱收费问题的整治不能很好地与鼓励学校进行特色经营结合起来,结果学校都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家长在这一过程中也深受其害。
对公立学校,政府实行强制多元化,对民间自主办学和学校自主运作,政府表现出来的则是管卡压,这两方面是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一以贯之的是强制性的教育制度变革思路,以及政府在各类教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传统定位。我们在这里批评“强制”,不是否定政府在公立学校办学体制多元化过程中的主动地位,而是批评它缺少有效的沟通,缺少对自我角色的清晰定位以及与此相伴随的自我转型,凭借少数人的长官意志行事。这从表面上看似乎还有利于提高教育制度变革的效率,其实常常导致教育制度变革的反复和低效,因为它很难全面考虑相关利益群体的要求,而且很难避免出现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有效监督问题,因而经常导致“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改革僵局。
(五)“地下产业化”问题
迄今为止,办学多元化与教育产业化之间仍没有合法的沟通渠道。我们允许办学多元化而观望教育产业化,结果导致学校教育的“地下产业化”,并增加了规范化管理的难度。当然,这里所说的“地下”并非各级主管部门完全不知情,而是相对于法律的规定,这些现象不能登大雅之堂。在上级主管部门检查的时候,这些必须小心地加以遮掩,尤其要防止家长的投诉。至于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他们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相互通风报信,以防在自己辖区内被上级领导发现存在着“顶风作案”的情况。
在广东的教育调研中,我们发现了公立学校地下产业化的某些线索:
1.接收择校生。公立学校被明令禁止择校(公立学校只收“借读生”,不收“择校生”,择校需到私立/民办学校)以后,公立学校的择校就转入了地下,但规模上并没有明显的缩减。规定公立学校班额的努力也起不到效果。学校通常在一年级有控制班额的激励,因为有上面的检查。但一往上走学校就拼命招揽择校学生。在择校费的收取上,学校也完全抛开了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
2.开办课后托管和兴趣班等追加服务。广东的一费制改革将原来比较灵活的“按实结算、多退少补”原则以代收代支形式收取的费用,变成了按统一标准硬性收取的书杂费和住宿费,并且规定未经省政府批准,任何部门(单位)和学校均不得擅自立项收费,对学校开展特色教育服务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学校只得将原有的有偿教育服务项目转入地下。以开办兴趣班为例,很多地方都以社区服务中介组织的名义开班。由于增加了中介服务并因此增加了中介费用,学生需要交纳的费用实际上反而是增加了。
3.直接向家长伸手。学校经常以各种名义直接向家长伸手。许多学校在申报等级学校的过程中,都曾以“自愿集资”的名义向家长伸过手。在这种情况下,当地教育主管部门一般只是要求学校做得手脚干净点,不要出漏子。
就近入学制度加剧了公立学校的地下产业化进程。尽管国家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招收择校生,但在同一地区,“名校”与“弱校”间的现实差距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择校问题。此外,即便某一教育层次的学校实现了均衡化发展,其所对应的上一教育层次学校发展的不均衡,也会引发择校问题。这些行为在择校本身不合法的前提下,必然引发不正之风。不少家长为让孩子进名校而四处拉关系、批条子,甚至利用工作之便施加影响或换取特殊照顾,不仅增加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量,造成学籍管理上的违规操作,还助长不正之风。有的家长为择校而通过各种渠道突击转户口,造成“人户分离”、“搭户”、“空挂户”等混乱现象,失去了就近入学的真正意义。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学校对前来择校的学生家长,往往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假如一次性的择校费是3万元,对有些人他们就要求多给,原因是学生的家庭条件好,而且择校的意愿非常强烈,理由则常常被说成是学位紧张,又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弄不好会受到上级的处罚)。而家庭条件一般的择校生则可以适当减免几千元,尤其当学生的质素很高的时候,因为学校都是喜欢既能招到好学生又能赚到择校费的。但领导推荐的学生则不用说就可以享受更大的折扣甚至免收择校费的待遇,因为这一交易过程能增加学校与该领导的沟通,从而为学校乃至校长个人今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也正因为如此,择校在很大程度上就演变成对校长和领导的拉拢、巴结和攻坚。
就私立/民办学校的办学实践而言,尽管我国法律规定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由于对私立/民办学校产权关系及产权运行机制缺乏明确规范,私立/民办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仍然出现了种种弊端:一些办学者为规避投资风险,想方设法在短期内收回成本,致使私立/民办学校有成为“学店”之嫌;少数私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钻法律空子,使办学资金不流入学校账户,如有的举办者在学校之外再成立一个公司,资金就以借贷的名义借贷给学校,由学校向公司支付利息,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把钱撤走;某些企业或个人用办企业的方式来办学校,利用国家对教育的优惠政策,直接谋取经济利益,造成名为学校而实为企业的“学校企业化”现象;许多私立/民办学校的组织机构及运作方式就如同私营企业一般,学校的决策、执行和监督集于举办者一身,致使学校每日都处于实际的危险之中。
在我们收集到的一深圳私立/民办学校筹划举办高中部的可行性报告中,对办学形势做了这样的估计:“中国教育消费潜能达5千亿元,目前在5万亿元的居民储蓄中有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我国现有普通中、小学生约两亿人,现有高中生约2千万人,每人如果平均5千元择校费用支出,约有11000亿元以上的潜在收益,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预计深圳全市2002年在校小学生40.0 4万人,初中生13.9万人,高中生9万人,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在校学生近37万人,所占比例达全市中小学生总数的55.7%;香港教育署公布,今年达到级别分数线而没有学位上学的中学生达8万人之多!从香港人来深购房看,占香港总人数10%,这几十万港人来深居住,其子女必入读深圳的‘贵族学校’;大批的外来移民,包括周边地区移民,无论从家长的角度或是从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讲,有条件的,一定希望到现代化大都市的深圳‘贵族学校’入读。”从这份内部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私立学校办学的真实动机。
在我们对广州市一家私立/民办学校的调查中,该学校校长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学校共招有学生2400多名,每人每年缴纳45,000元的学杂费。根据他们自己的粗略估计(他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像他们那样的一所学校如果能招到1000名左右的学生,就可以维持收支的平衡了。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个数字肯定是保守的——该校每年将赢利6300万元。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即便这所学校还在还贷的阶段(实际上对他们而言这个阶段早已过去),纯赢利的日子也不远了。你能想象他们把所有这些资金都放到教育事业上来吗?那很快会克隆多少个那样规模和档次的学校?在我们其他的调研中也有知情人向我们透露,私立学校只要经营得当,利润率都有50%左右。
而且,不但是国内资本介入了私立学校的营运,国外资本也通过曲线途径进入国内的义务教育市场,如在国内找一个可靠的代理,以他/她的名义开办学校,但主要管理人员都由背后的老板自己委派,尤其是财务人员,外人根本不得而知其中的奥妙。只知道深圳有些有国外背景的学校通过北京的渠道向国外转移利润,至于具体的方式,则不得而知。而根据国务院2003年3月1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外合作办学者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
据我们了解,公立学校分配办学收益的方式主要是建立帐外资金,并通过集体福利或奖金的形式发放,这些都是学校的隐秘知识,有人戏称“连老公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私立/民办学校将不可分配的收益据为己有的方式则有多种。其中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将各种实际支出都列入教育或办学成本,或者通过转移收支的方式——设置帐外资金的一种新措施——而启动利润分配过程,或通过“关联交易”将各项办学开支转换为个人营利,“以校养店”。对于转制学校,这些学校很多本质上是公立学校,但贴上了“转制”的标签,就可以博取当地政府的厚爱(巨额投资)和青睐(选调优秀中青年教师、比其他公立学校提前一个月在全区招生),并光面堂皇地向每个学生收取五六千元的赞助费和其他学校不敢收取的费用,在学校收益分配上也拥有更大的权限。当然,对他们而言,由于存在着逃避政府管制的激励,暗箱操作依然存在。
我们可以根据收益性质及其流向将地下教育产业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福利型。这是公立学校中最常见的地下产业类型,在带公立性质的转制学校中也是如此。“滥发”的奖金也属此列。另一种是利润型。这是私立/民办学校或私人参股学校的牟利类型,受益主体是办学的投资人。还有一种是租金型。这种地下产业的受益主体主要是政府官员和校长,在现行多元办学体制下普遍存在于各种办学形式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问题主要来源于政府管制。其根源在于政府依旧受传统、习惯和利益所限制,忽视自生自发的教育力量,未能处理好自身与学校、市场的关系,不能在教育主管部门、投资者/举办者、学校管理者、教职工和学生及其家长之间进行有效的利益协调,结果造成了新的条块分割和教育管制,不同性质和类别的学校之间彼此不沟通,“教育货币”(在此指主要教育权利、国民资格、政策优惠等)不能在它们之间自由兑付,不同系统奉行完全不同的规则,根本没有衔接和相互学习的可能性。而在通过正当的途径不能获致足够激励的条件下,市场自发力量不得不以扭曲的方式为学校的发展开辟道路。
这样一来,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与教育的自主化、平等化、开放化、规范化和产业化之间,就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当然,按初衷,多元办学体制的建立最初主要是为了解决教育经费紧缺的问题,并不是要引进诸如教育自主化、开放化和产业化等因素。它所要达到的教育平等化和规范化,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权利平等和依法治教也有相当的距离。但现在如果仍只是从经费角度考虑办学体制多元化问题而忽视教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受教育者的权利问题,确实已经是远远不够了。事实上,由于忽视这些问题,我们教育发展的步伐已经大大地被延缓了。大量的民间教育资源在这一过程中被闲置或流失,大量的受教育者被简单粗暴地对待,素质教育的理想始终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就是明显的例证。
三、问题解决的根本思路及政策建议
而要克服政府的教育管制,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与教育的自主化、平等化、开放化、规范化和产业化之间的联合,真正解决教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受教育者的权利问题,在教育中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就应该成为解决我国多元办学引发的现实问题的根本出路。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对教育性质进行重新认识。
(一)教育服务性质与教育产业市场
在支配现行多元办学体制的教育理念中,最为核心的,是对教育服务性质的认识。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对多元办学采取管制立场,除了考虑部门利益和社会稳定等因素之外,关键是在对教育服务性质的理解上不能取得突破。其中,基于经济学视角的教育的公共性、基于政治学视角的教育的公益性和基于教育学视角的教育的精神性,都曾强化了政府的管制立场。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的公共性。在我国,一直由公共教育体系提供的教育服务不仅是一种纯公共物品,而且是一种垄断性的公共物品。因为这种公共教育体系型塑了一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观(反映在实践中主要就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帐),以至于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的增长,而排除任何个人对它的分享却要花费巨大成本。长期浸淫于这种教育实践,再加上我们以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导致人们普遍以为教育就是一种纯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出面加以生产和提供。近些年来,人们开始认识到:教育的这种纯公共性并非教育自身的属性,而是社会制度安排赋予教育的一种属性,正是政府的一元化教育供给机制造成了这种虚构的公共性质;而就教育自身的属性来说,它应当是一种准公共物品,虽然在消费上不完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可以由市场方式或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有效提供。认识到这一点应当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问题之一仍涉及对公共物品的理解。应当说,所谓公共物品,就是人人都有资格享用,而且享用的同时及之后并不排斥或减少他人享用的物品。不过严格地说,公共物品利益上的非独占性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纯粹是一种效率特性——要想独占或排他需要支付巨额成本,而这本身是低效的。当然,对绝大部分公共物品而言,完全不排他也是缺乏效率的。根据这一理解,判断某个东西究竟是否是公共物品,不能单纯看该物品自身的性质,而要看当时的制度条件和人们排斥外人对该物品分享的技术水平。 当前国内有学者认为:“教育不能同时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准私人产品。”理由是“按公共产品理论对产品属性的分类,是从产品的消费特性出发的。” 言下之意为,教育在任何制度条件和技术水平下,其消费特性都是一致的,而且是统一的,消费上的非完全排他性是教育自身的本质特征。其间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教育的消费特性也可能受制于不同的制度条件和技术水平,因而片面强调其单一的“准公共性”。问题之二则在于:在对教育服务性质的这一认识中,市场常常只是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而不是产业运作方式看待的,结果教育的市场化和教育的产业化在这里是分家的,因而势必又重蹈原有体制激励不足的覆辙。
受这两类教育服务观的影响,当前教育理论界要么把教育服务看作一种准公共物品,同时竭力将教育市场的作用限制在资源配置的有限范围;要么把教育看作一种公共物品,因而强烈反对市场机制对教育系统的介入,结果都失之偏颇。应该说,教育服务至今已然存在着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区分。有些教育服务现在已明显属于私人物品的范围,并且是由公开或半公开的营利性组织或个人提供的,如家庭中的补习教育,又如私立学校中的教育服务;有些则属于由国家(实际上是由国家垄断市场)提供的私人物品范围,如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在这些教育形式中,尽管在一定的范围内增加一个人的教育消费不会增加教育支出,即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但这种教育的消费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只有个人支付一定的教育费用才能享受这种教育消费,因此这种教育服务实际上已高度产业化了;有些教育服务现在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围,它们虽然在消费上不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但可以由产业市场(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而不纯粹只是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有效提供,象弗里德曼教育券计划中的初等学校教育就是如此;还有些教育服务现在仍属于纯粹的公共物品,但有变为准公共物品的制度和技术潜力,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服务就是如此;此外,有些教育服务现在还看不到变为准公共物品或私人物品的可能性,如军事院校的教育服务和党校的教育服务等。
由于教育或者具有公共性,或者具有私人性,或者是这两种属性的某种程度的混合,片面强调教育的公共性或准公共性如今都难以阻挡教育产业市场的进攻,结果,有些学者转而强调教育的公益性,希望借此避免在教育供给方式上的论争,同时又维系教育中的实质正义。公益性与公共性有一定的联系,个人的教育行为具有外部效应、溢出效应或社会效应。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对他本人有好处,对他所在的社会也有好处。而一个人在教育上的一无所有,对于他所处的社会而言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此,即便是个人的教育行为,也是一项对公众有益的事业。这就是教育的外部性,是我们前面所强调的教育的公共性的一个方面,即消费上的非排他性;也是教育公益性的经济方面,即公民个人的教育行为客观上具有利国利他的社会效果。教育的外部性以及由此衍生的公益性一方面要求国家或政府出面理顺教育中的产权关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家和政府对这一部分“意外收获”提供与之相称的激励、补偿或扶持。
但公益性不完全等同于公共性,它主要是教育的一种政治属性而非经济特性。教育具有政治上的公益性,意味着它是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石。因为现代民族-国家不是建立在一些实实在在的社群因素如血缘、姻缘、地缘、种族、宗教、语言或隶属关系等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公民身份与认同情感的想象、一种建立、保卫及行使国家主权的共同意志的想象之上的,或者说,是建基在公民平等参与行使国家主权之上的。 这样,为所有公民提供一种公共的教育服务,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石之一。但国内许多学者对这种教育公益性的认识,还停留在市场经济之前的水平上。受“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均衡器”观念的影响,他们很多时候将政治上的教育公益性等同于教育的福利性,即把教育理解成一项福利事业,因而经常不切实际地要求教育在实现社会实质平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按道理,说“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均衡器”也没有错,但教育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具有这种公益性,则是一个必须认真加以考虑的问题。不能因为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均衡器,就片面夸大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不切实际地增加政府在教育投资中的责任。实际上,作为政治性公益事业的公共教育必然是有限的,政府在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这既是政府的财政能力问题,又是政府的责任范围问题,而且主要是政府的责任范围问题。一句话,政府没有为所有公民长期无偿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义务。因为个人作为现代社会自主的主体,并不完全也不能完全归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否则民族-国家就必然蜕化为现代专制国家。所以,真正作为公益事业的教育,其实主要只是必须由国家提供的基本教育服务,这部分教育服务主要体现在义务教育之中。我们通常倾向于夸大政治上的教育公益性,赋予教育不切实际的救世主形象,以致造成了教育中严重的平均主义和福利主义倾向。
因此,教育的公益性是以教育的“私益性”为补充的。它虽然要求为公民提供(不一定是直接生产)基本的教育服务,并确保公民个人客观上利国利他的教育行为得到与之相称的激励、补偿或扶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对公民的教育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而所谓教育的“私益性”主要包括:教育具有个人效益;教育是一种可以经由个人自主/选择、因而也就是一种可以由个人自我负责的个人事务;个人可以追加教育投资等。承认教育的“私益性”既有助于扩展个人可以享受到的教育的范围,也有助于改变个人享受教育的方式。在公益性“独霸天下”的条件下,人们只能享受到国家提供的教育服务,而且只能作为“受教育者”接受由国家配给的教育服务。认识到教育的“私益性”,我们就有可能在国家提供和法定的基本教育服务之外对其他教育服务进行自主选择。
当然,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的“私益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明显,经济意义上的教育公益性是直接与教育的“私益性”联系在一起的,是在私人教育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教育公益性,说明教育并非从最彻底的意义上来说都是公益事业,而是兼具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双重性质,公益性只是教育属性的一个方面。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承认教育的“私益性”,就很容易推出教育的产业性或营利性结论,而这是解决当前多元办学体制的现实问题的重要前提。现行的基于行政集权和条块分割的多元办学体制否认教育的“私益性”,把通过市场化运作提供的教育服务仍然看作是或限制为一种公益性的服务。因此,它虽然认可教育的市场供给方式,但坚守教育的公益性,多次否决私立学校和民间集团提出的“投资教育可以营利”的请求。这是力图通过对资源配置方式和产业运作方式的分割来达到对教育公益性的维护,结果导致了运作过程中的超经济强制。
更为重要的是,由国家或政府负责提供的基本教育服务与教育的营利性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通常,我们把这一部分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多也只是把它与受到严格限制的营利性组织联系在一起,让“营利”蜕化为“合理回报(盈利/赢利)”,并且把经由营利性组织提供的教育服务看成对公共教育服务的一种无奈的补充。而在以往,我们更是明目张胆地排斥营利性教育。即便对私立学校,也不放弃教育的非营利性理想,最多允许投资者获得固定的合同收入而不能拥有学校的剩余索取权,哪怕造成触目惊心的地下产业化也在所不惜。结果,由政府机构或其他非营利性机构直接提供的公共教育服务导致了教育的短缺和低效,尤其是导致了优质特色教育的短缺和低效,并且在实践中还导致了对公民个人教育选择权的限制。
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教育公益性与教育营利性的关联明显凸现了出来。然而,除非有足够的合法激励,否则基本教育服务的提供要么成问题,要么势必造成严重的“地下产业化”倾向。近十几年来,在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办学实践中,就出现了我们的政策规范屡禁不止的“乱收费”行为。尽管我们仍三番五次地强调,教育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但教育中的地下产业化仍然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并且有强烈的自我辩护倾向。这是一种合法激励不足条件下的自我激励。应当说好在有这些自我激励,这些激励在我们领导的眼中也并非那么令人深恶痛绝,非得斩草除根而后快,而是刻意容忍和上下遮掩,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做一些曝光和处理,否则真不知我们的教育事业会再度萎缩到什么地步。然而,为了教育发展而容忍教育中的地下产业也导致教育中出现了严重的“钱权交易”和“权力寻租”倾向。这些问题难以容忍,必须通过推动教育产业市场的规范化最终加以解决。
这么说有人也许难以接受,他们会争辩道:基本教育服务虽然可以交由教育市场提供,但完全可以与教育产业化保持适当的距离。这其实是一个国家能否足额提供基本教育经费的问题——如果经费能足额提供,营利性的组织和个人就有足够的激励经由产业市场提供基本教育服务。当然,这里的办学收益率受制于国家的教育投资水平,而这本身又是见仁见智的。然而,存在着一种即便是最激进的教条主义者也难以反驳的营利途径,那就是通过“增产节支”而营利。如果我们按照学生实际人数拨发教育经费并且不降低经费水平,即便我们坚决杜绝或打击各种乱收费现象,我们也决不能禁绝通过降低教育成本而营利。有人也许会说,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下调生均教育经费。但一旦下调生均教育经费,节约教育成本的努力也就烟消云散了。不但如此,教育中的任意挥霍行为还会难以遏止地增加。因此,除非我们不改革教育财政体制(即仍然坚持按照确保学校基本运作的标准直接拨款并专款专用),继续听任现有教育财政体制的折磨,否则,教育中的营利冲动必然增长。而不改革教育财政体制的后果是,我们的学校将依然面临激励不足和任意挥霍的困境,而且将继续面临种种不断恶化的地下产业化活动的诱惑。
此外,办学者还可以通过提供追加、优质或特色教育服务谋取边际利益,这一点也应当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前面我们提出,必须由国家提供的基本教育服务主要表现为义务教育服务。但关于义务教育,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那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不纯粹是义务教育服务。有许多超出义务教育范畴的教育服务出现在我们今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中,这些教育服务既包括那些高于国家标准的优质教育服务,也包括那些超出国家标准的校本特色或追加服务。因此,即使在义务教育阶段,也不能完全要求国家和学校免费提供全部教育。而限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只能提供基本教育服务,或强迫它们提供免费的优质、追加或特色服务的政策建议,哪怕只是听一听也只会让人对它那拙劣的激励机制哑然失笑(可惜笑归笑,这样的事每天还在发生,“一费制”改革就是如此)。
《民办教育促进法》所倡导的“合理回报”概念和标准也许还有进一步明确的潜力,但当前立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对“营利性”的全盘否定态度仍引起了我们的严重不安。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教育中的营利行为就真的那么万恶不赦而且难以以市场竞争的手段加以有效的调控?政府和学校的广泛存在难道就真的对这种营利行为毫无约束?难道开放教育市场真的会出现流言中的“唯利是图”?将学校分为营利性的与非营利性的难道就真的难以驾御?我看就不然。人们在这里缺少一种系统眼光,总是从单个学校单种体制出发考虑问题,没有把营利性学校及其教育服务放到整个教育大市场中去思考。结果,我们总是操了一些不必要操的心,担心这类学校发展不好,担心它们招生困难,担心学生在其中受骗上当。以至于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它们就成了不可放纵的潘多拉魔盒中的恶魔。
有学者为了坚守教育的公益性,进一步提出了教育的精神性问题。他们多次强调:“教育的价值基础…决定了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通过对个体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促进个体身心发展,使个体社会化,并最终使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学校的教育活动从根本上说不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利润,而是为了造福他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是从文化、精神、体质、社会诸方面开发人的潜能,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各种基本条件的事业。因此,由公益性取代古代教育的私益性就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任何一种教育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前提。” 在他们看来,现代教育的价值基础决定了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公益行为。也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把建立在自愿贸易关系基础上的教育提供方式,称为“市场化公益行为”。
这种观点实际上仍只是在强调教育的外部性。它把具有外部性的教育行为都看成是公益性行为,根本就没有看到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的私益性之间的区分,而且也把教育功能与经济功能不恰当地对立了起来,根本就没有看到对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进行有效激励的必要性。实际上,说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与说教育是一种以成本收益计算为基础的经济活动,以及与说教育是一种既具公益性又具私益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它们都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得出的有关教育服务性质的兼容结论。当然,教育过程作为一种长期过程,以及师生交往导致的学生对教师的依恋,在教育选择方面都将造成有利于学校控制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择学校的局面。这样,如何确保教育中的“消费者主权”,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但即便如此,受影响的也只能是教育市场化的程度和方式,而不能要求将整个教育事业都变成一种公益事业。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在近代制度化教育中,人们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自诩,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立场,自然不允许把教育“贬为”知识商品的买卖。但现代教育强调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终裁决者,不能把价值判断强加于人。这时,进行知识商品的买卖,就不是对教育的贬低,而是最合理的教育形式了。而且,市场交换实质并非物的易手,而是产权的让渡,因此,对市场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产权和自由的尊重。 况且正像薛兆丰所说的那样:“市场连一棵草的价值也不会低估,何况是科教呢?” 因此,当有学者强调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教育公益性与资本寻利性的悖论” 时,我们的看法则是,悖论不悖论关键在于我们对待公益性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把整个教育都说成是公益性事业,当然存在所谓的悖论。但如果能够看到在公益性之外还有私益性的存在,对公益性事业的扶持需要有以私益性为基础的激励,以往的“悖论”完全就可以自行消解。
现在看来,既然教育的公共性主要只是源于我们以往的技术基础和制度框架,在现行教育体系内部,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发生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分化,片面强调教育的公共性已难以站住脚跟;既然教育的公益性有其限度,政府在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既然教育的公益性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的特性(与此相关的还有教育的私益性方面),其全部内容也不过就是为公民提供基本的教育服务,并确保公民个人客观上利国利他的教育行为得到与之相称的激励、补偿或扶持,而且在教育的公益性与教育的营利性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既然教育的精神性不足以成为确保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共性的最终决定因素,也不足以成为抵挡教育中的产业市场进攻的最终法宝;既然个人在自我的教育问题上应当拥有更广泛的发言权和自决权,我们就确实有必要以超前的眼光、务实的心态,超越围绕教育服务性质问题而展开的意识形态论争,以市场化的思路克服现有多元办学体制的制度性缺陷,在努力追求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同时把握市场化、产业化的大局。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强调教育产业市场,并不是要否定国家或政府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限制和转换,从而建立一种“有限教育行政制度”:一方面,那种事无巨细的集权管理必须得到抑制,教育管理必须从教育中的私人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教育公共领域之内的政府职责必须得到加强。 这实际上牵涉到对市场机制的理解问题。在樊纲看来,“所谓的市场经济,简而言之就是由民间自由交换实现‘私人物品’的有效率生产,而由政府负责安排公共物品的供给这样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因此,要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做的事情只在于使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从原来的一些职能中退出来,更好、更强有力地执行另外一些政府应该执行的职能。“所谓‘削弱政府’,只是要削弱它在‘私人物品’生产中的作用,而不是要削弱它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的作用,相反,它在这方面的职能还需要加强而不是削弱。”
可以以义务教育为例来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有学者指出:为确保教育公平,改善中小学教育的品质,抑制恶性择校和升学竞争,使学校教育正常化,必须推行教育均衡化的政策。其基本措施包括:平均分配教育经费,使学校的校舍、设备等硬件水平大致相似;公平地调配师资、校长,或实行定期轮换,以保证大致相同的师资水平;按学区平等地接受学生,使生源质量大致相似,等等。这在我们看来是不能苟同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且可能为少数人恶意地加以利用。在我们看来,强化政府在义务教育中的责任,主要是强化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提供、机会和权利保障方面的责任。即便要均衡化,也只能是个人层面上的权利均衡化,即首先要确保受教育者有基本的学习条件,其次要确保受教育者对这些学习条件的自由支配(当然是用在学习上的),最后是要确保受教育者在自由支配自己的学习条件的时候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学习需求。将均衡化不切实际地推及学校和学区的发展方面,并希望借此将学生困在原居住地接受学校教育,完全是与市场化的大局背道而驰的。
而当我们承认教育产业市场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市场制度的存在。因为市场不是物,而是一系列制度的聚合。那么,真正的教育市场制度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这可根据一般市场制度的构成进行推断。市场经济有三大支柱性原则——绝对物权、自由契约和公平竞争,它们分别对应于财产权制度(规定财产权利的界定和地位)、市场交换制度(规定财产权利的让渡和取得)、公平竞争制度(规定市场交易活动的权利与责任)三大市场制度。 教育市场制度主要也就由这三方面的制度构成。在我们今天的教育中,这三个方面的制度都严重欠缺。首先是没有明确合理的财产权制度。公立学校体制所有权模糊和产权配置不当的问题已众所周知,个人的教育权利更是受到严重忽视,由此导致了学校管理不善和个人教育不自由等一系列问题。其次,教育市场交换制度更是极不完善,一种竭力把价格机制驱逐出公立学校体制的努力至少在目前仍占着上风。象今天“择校收费”在公立学校体制中受到这样严格的控制就说明了这一点,各地之间的教育壁垒的存在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最后,公平竞争制度在教育中也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存在的都只是一种基于等级区分和条块分割的教育局面。因此,如果说我们也存在某种教育市场的话,这种市场只能说是一种高度分割和管制的市场。
可惜我们现在虽然部分认可教育的市场供给方式,但仍坚守公立教育的主体地位,限制社会资本的自由进出。同时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追求教育平等,却忽视公民的教育选择权,限制而不是鼓励公民个人的自主教育消费。其间的错误,在于无视教育公益性的内容和实现形式在新形势下所发生的积极变化,继续以隐晦的方式将教育事业等同于全民的福利事业,否认教育中的国家责任的有限性,同时对民间自发力量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的成效的信心严重不足,并不切实际地将教育的教育功能与经济功能对立起来。由于将教育选择导致的个人教育状况的分化看成是对教育公益性的侵犯,这种对教育结果平等的强调在实践中导致了对公民个人教育选择权的限制:不但限制那种基于个性的分化,而且限制个人自主的教育消费总量。
(二)教育券:核心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公立学校效率低而政府又必须为公民免费提供基本教育服务之间的矛盾,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1955)一文中,提出了一种以教育券计划取代公立学校的设想。所谓教育券计划,就是政府向父母按生均教育经费标准发放教育券,父母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学校再把挣到的教育券向政府索取资助。这一计划的核心理念,便是在教育中引入市场经济的机制,由家长(学生)自由选择学校来达到优胜劣汰、全面提高学校质量的目标。
教育券计划自提出以来,在国际教育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但实践上的进展一直甚缓。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浪潮的影响,世界各国对教育券计划的研究和尝试突然加速。目前,美国已有一州两市正式实施由公款资助的“教育券”计划,另外有10个州建立了私人和私立机构资助的“教育券”制度。其它如英国、瑞典等发达国家,以及智利、哥伦比亚、波兰、孟加拉国、危地马拉等发展中国家,也都在推行这一计划。我国台湾“教育部”也于1995年正式将教育券列入实施计划,并先后在幼儿教育和私立高中职教阶段进行。
2001年9月,浙江省长兴县在我国大陆率先进行三种“教育券”制度试验:一是扶持民办学校、面向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义务教育类扶持型教育券,面额为500元;二是促进职业技术教育,面向职业类学校的职业技术类引导型教育券,面额为300元~800元;三是为了补助因特殊原因丧失或部分丧失学费来源,无力支付必要的就学费用或因突发事件造成家庭特别困难的本县中小学生的困难补助类扶贫型教育券。这场改革犹如一股春风,引起了研究者多方的兴趣。可惜直到目前为止,这场改革仍然有着诸多的缺陷,一种竭力把价格机制驱逐出公立学校体制的努力即便在这里仍占着上风,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1.对教育券理论的争议及其反思
教育券的真正意义在于使学生及其家长真正成为教育的自主消费者,使学校和教师真正成为教育的自主生产者,通过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打破国家对教育的行政垄断和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促进学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从而确保国民教育权,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由于它与现代公共教育体制乃至我国现行的基于行政集权和条块分割的多元办学体制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路和逻辑,并将带来教育中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机制的深刻变化,从而给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带来极大的冲击,在国内外都引发了严重的争议。对此,我们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
(1)教育券是否能够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
我们认为,教育券强调自由竞争,在此体制中,各校必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以求办出品牌和特色,争夺学生及其家长手中的教育券。这样,多元化的教育服务必然能够出现。因为学校只有办出特色,才能满足公民的多元教育需求,获得自我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如此,学校将因竞争而提升其品质,学生也将因此而享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服务,从而达到双赢的结果。而以往公立学校相似性颇大,主要就是由于政府计划难以适应教育需要,反而型塑/扭曲教育需要以迎合制度框架而造成的。
反对者则经常强调: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竞争可以改善学校或是学生的成就。而且即便教育券确实能够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但这也只是对有钱人而言的。贫穷家庭的学生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事实上很难行使教育的选择权。因而所谓提供更多的选择,对他们而言其实只是个美好的谎言。而如果贫困家庭在这一计划中没有得到更大的好处,即便他们的处境没有恶化,其他人群处境的改善在他们看来在道德上也是成问题的。因为这进一步拉大了社会各阶层的差距,导致了更大的社会不平等。
我们认为,多元教育服务,不用说在教育券计划中,就是在今天的多元办学体制中,也已经不可遏止地出现了。教育的这种多元化趋势,主要就是随大一统的公共教育体制的瓦解产生的。在更为宽松的教育券计划中,随着阻碍自主多元化的因素进一步被清除,优秀的校长和教师不但有更高的市值,而且拥有更大的事业舞台,由此将刺激更多的个人和机构改进课程、教法和学校管理,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教育多元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可惜,在支配反对者的思路中,总是存在一种强烈的嫉妒心态,而且总是倾向于忽略:只要有合理的制度设计,各种人群就将都能够在其中受益,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人们要么只能享受到公共教育的好处,要么只能享受到私立教育的好处。
(2)教育券是否有利于促进学校的良性竞争
我们认为,只有在彼此都能自由出入的情况下,才能剥夺私立学校的剥夺性质,也才能剥夺公立学校的特权性质,从而才能最终剥夺笼罩在各类学校上面的强制性质。因此,通过教育券建立教育服务的统一市场,是打破公私立学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废除公立学校享有固定生源、固定经费的特权,迫使公立学校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最有效的方法。也是废除私立学校在择校和收费方面的特权,迫使他们与公立学校争夺以往被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排除在外的生源和资金的有效方法。
反对者认为,支撑教育券的是对于市场自行调节能力的信任,以及对家长判断和选择能力的信任。但实际上教育市场有其特殊性,教育监控与选择的交易成本极高。而且,家长的选择并非毫无限制,除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外,他们还必然同时受到文化水平、价值观念、交通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教育性质本身的限制。因此,良性的市场运作不但很可能不能建立起来,而且很可能造成有钱学生拥向私校,贫困学生困在公立学校的局面。而公立学校由于必须承担起形成社会凝聚力与共同价值观的职能,又必然勉强维持其存在,这就势必导致公私立学校的不平等竞争。
对此,我们认为,支撑教育券的不是对于市场的无度信任,而是对教育中的消费者主权的尊重,以及对公民教育选择权的平等保障。而且,教育券计划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优点的折衷体制,它一方面维持了政府的支付责任,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学生(家长)的选择权,而不是把一切托付给市场。我们真心地希望所有提供义务教育服务的学校都能如此幸运——既能有类似于计划经济的那一套好处,又能有市场经济的那一套好处。因此,考虑到教育选择的特殊性(成本较高),教育券计划可以被设计成那种更利于发挥政府和家庭的监管作用的形式。在这种竞争体制中,大多数公立学校将被通过适当改制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至于少数公立学校迫于客观情势而必须“勉强”存在,也可以以特殊方法加以处理。那就是继续按照旧有体制运作(如有机会也可以交由非营利性组织经营)。实际上,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也是政府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3)教育券是否有助于促进教育机会均等
我们认为,教育券是平衡学生及其家长权利,将教育选择权真正还给家长,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真正自主平等的教育机会的可靠方式。在教育券计划中,每位学生都可以凭教育券选择适合自己的学校,而不受原居住地区或地缘身份的限制,这将使学生的受教育机会更趋公平。它所信奉的自由择校进一步体现了现代教育的民主原则,不仅为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如低收入者、少数民族等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也为有特殊专业或能力而没有经济实力实现其价值的人提供了机会。而且,完整的教育券计划也承认富人子弟在教育中的国民待遇,确保了全体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但反对者认为,从实际上看,许多家庭,特别是教育程度较低、经济状况差的家庭可能无法获得全面或真实的市场信息,他们可能无法了解当地或附近学校的真实情况,这样必然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选择。即使选择了,也可能由于住宿、交通等原因而放弃。此外,教育券之实施对象包括私校学生,而选择私立学校者只能是那些有更多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的子女,因而教育券只是减轻了富裕家庭的负担,损害了公共教育的普遍性、公平性,可能造成社会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加剧和扩大。
对于这些异议,我们的观点是:教育券给人们提供了选择教育的机会,但并未要求个人非得做出选择。那些不选择者的处境实际上也不会因为实行教育券而降低(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多出了以前所没有的选择机会/权利,因而增强了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而其他的人则从中获得了增益,符合帕雷托优化的条件。此外,教育券计划本身可以考虑到贫困儿童在接受基本教育服务时机会成本较高的特殊性,通过对他们适当增加补贴的方式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至于因为实行教育券计划而导致教育经费流向私立学校,也不能说它就损害了公共教育的普遍性和公平性,因为选择私立学校者在这一过程中不过是享受了他们本该享受的国民待遇,而私立学校也不过是因在满足公民个人的基本教育需求方面的成功而获益。
其实更为重要的是,教育券计划并非只有符合了上述三个问题所隐含的实质性标准才具有合法性。尽管在此我们一再强调,从总体上看,教育市场化是有助于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促进学校的良性竞争和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但教育市场化的最终基础是对公民个人的教育自主权和民间社会散在的教育资源的尽可能多的尊重,而不是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简单承诺。事实上,教育服务不能为多元而多元,学校之间的竞争不可能也不必要达到完全竞争的程度,而结果意义上的教育机会均等与教育市场化是背道而驰的。既然如此又如何能通过教育市场化摆脱办学困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忘记我们前面说过的见解:我们不是为了某个特殊/具体的实质目的而倡导教育市场化,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克服政府的教育管制,实现办学体制的多元化与教育的自主化、平等化、开放化、规范化和产业化之间的联合,真正解决教育发展的动力问题和受教育者的权利问题。
2.我们对教育券的理论构想
反思我国浙江长兴的教育券实践,不难看出,这种教育券仍停留在对部分学生的简单资助上,期望解决的主要也是教育的公平和平等问题。由于不能自由兑付,家长(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并未真正得以落实,这与教育券计划的精神实质其实有很大的差异。须知,教育券不单纯是一个教育扶贫措施,也不单纯是政府对学校资助方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确保政府对公民个人的资助,确保家长(学生)的教育选择权,从而以此为基础,促使学校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益,真正满足公民的教育需求。可见,“教育券”不能离开选择,家长(学生)的教育选择权是教育券的基石和核心。
而要确保学生及其家长的教育选择权,就必须建立统一的教育市场。因此,教育券计划的构思涉及各方面的相关制度设计,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有对教育制度的广泛思考。简单地把教育券计划限制在教育券的设计、发放和管理等有限方面是不负责任的,需要有对各利益主体的相关政策规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建构起教育券制度的体系。下面,我们将结合对各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重新界定,来阐述我们对比较完备的教育券计划的理论构想:
(1)学生及其家长
学生及其家长应享有获得与国家规定的基本教育服务相称的教育券金额(应大致相当于某一教育层次的生均教育经费,而教育券总额应等于国家及地方的各类教育经费总额)的权利;享有对学校及其追加或特色教育的选择权;享有对学校教育的知情权;享有组建家长委员会维护自身权益的自主权。贫困学生及其家长在完成国家规定的基本教育服务中教育成本的特殊性必须得到考虑,他们有权在教育券中获得相应的追加资助。同时,学生及其家长有接受国家规定的教育标准的义务。
(2)教师
教师应有权与学校签订聘任合同;有权根据聘任合约和国家法律的有关规定获取报酬及其他福利;在超出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中,教师应有权获得与之相称的报酬;有权成立更具独立性的教师工会组织以维护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有权成立教师专业组织(如教师协会)以维护自己的专业自主。同时,教师有义务在国家教育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教育教学;有义务根据合同的规定开展各项工作。
(3)学校
能够参与教育券计划的学校应实行政校分开,享有完全的自主管理权,包括:对自身的财产应享有完全的支配权;享有完全的人事权,作为用人单位自主与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有权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教材和教辅资料;有权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范围内自定招生标准;有权自定超出国家规定的基本教育服务之外的优质、追加或特色服务的学费标准。同时,应切实承担校务公开的义务,及时向发放教育券的国家机构和支付教育券的学生家长提供有关师资、课程、教学、办学经费、设施设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基本信息;切实承担按国家标准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义务;切实履行教师聘任合同中约定的各项义务。不能参加教育券计划的学校则交由教育主管部门按原有体制管理,或交由非营利性组织按有关制度管理。
(4)教育主管部门
教育主管部门应从原来事无巨细的指令性、分配性行政转向指导性、服务性行政,从直接管理变为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实现有限行政和依法行政,切实加强对教育中的公共领域的管理服务,包括:提供公共政策和办学信息,为家长提供本地区内所有学校有关师资、课程、教学、办学经费、设施设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详细资讯;规范执行国家基本教育标准;保障基本教育服务的供给,包括为确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基本交通服务或交通补助;建立完善学券管理机构,确保把学券发给学区内每一个适龄儿童的家庭,为辖区内学生家长提供教育券的添补服务,并监督教育券的使用,防范教育券资金的流失;确保教育竞争的有序性等。
(5)各级政府
①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制定基本教育服务的国家标准,确保所有公民享受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教育服务,同时激发地方政府和个人投资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为此,应对贫困省区以教育券形式进行适当的经费资助并敦促各地对教育券进行必要的添补,以确保公民个人持有与基本教育服务相适应的教育券金额;确保国家教育券总额不低于原有的教育经费总额,同时确保教育券之金额必须随国民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公务员调薪幅度而调整;保护地方政府投资教育的积极性,激励其对当地居民和其他符合发放条件的家庭追加发放教育券金额;致力于消除教育中的地方保护,如逐步取消高考录取分数的地方差异;主动推进那些有利于个人投资教育的制度变革,如贷款助学制度的变革等。
②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应依法确保基本教育服务的提供,同时确保地方教育券之金额必须随地方财政增长情况、消费者物价指数与公务员调薪幅度而调整。为此,应向本区域内户籍学生发放自己所应承担的地方教育券补贴;向非户籍学生提供与其家长税收或居住年限相适应的教育券金额;考虑低收入阶层、劣势群体教育成本上的特殊性,为他们提供相对较高的教育券补贴,或者追加困难补助,并允许其教育券往高等教育阶段积累;设立地方教育专项资助基金用于扶持学业优秀又难以接受优质教育者并在教育券中添补,并允许由此提供的奖学基金用于后续教育阶段;建立地方担保的教育贷款制度,为贫困家庭提供长期教育信贷;在不能通过市场途径或非营利性组织为公民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场合,承担起为他们提供基本教育服务的责任。
3.过渡期的政策建议
教育券计划的实施将从根本上突破我国现行的多元办学体制,反过来,也只有打破现行的多元办学体制,教育券计划才有其革新意义。但任何一项政策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到可接受性或可操作性问题。就目前的制度状况及人们对教育券的知识储备而言,贸然全面推行教育券必然难以成功,而且必将造成混乱并铸成大错。因此,我们建议设立一个从现有的多元办学体制向全面的教育券计划转变的过渡期,在此阶段借鉴国内外现有的各类办学经验,先在小范围内针对特定学生或学校有限实行教育券计划,待条件成熟(主要是观念条件成熟)再通过一定制度性程序向下一阶段(教育券计划的全面实施阶段)过渡。
(1)过渡性的教育券方案
① 政策定位:强调可接受性和可操作性,在尊重家长选择的同时,首先给予社会公正与教育平等更大的关注,让社会的底层能够率先接受改革方案以降低改革成本,同时充分考虑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现行财政投资体制的框架内实行有限选择、有限资助。
② 发放区域:先以县或市为单位,再逐步扩展到市或省,在经济发达、有能力进行短期额外资助的地区先行改革。不同地区也可根据地区间协议就教育券计划进行跨地区的教育合作。
③ 发放对象:因进入私立学校、转制学校而不能按现有体制享受国民教育待遇的学生家庭;低收入的学生家庭,受到资助的这部分学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原校就读,用教育券支付优质、附加或特色教育费用;非本地户口但纳税达到一定标准或居住年限达到一定要求的学生家庭。同时,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因跨学区入学而被加收借读费的户籍生给予教育券资助。
④ 发放阶段:主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发放,因为它们提供的主要是基本教育服务,而教育选择又受到最大限制。考虑到这一阶段内部仍有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的区分,应按个人所处教育层次发放不同金额的教育券,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者所获得的资助应相对较多。
⑤ 发放金额:以生均教育经费为参照,但应给公立学校留出改革适应期(如10年),故对学生的直接资助金额可以逐年增加(如以每年10%递增),不能一开始就以生均教育经费的标准发放。同时也应根据上一学年学生人数情况的变化相应减少下一学年对公立学校的拨款总额。
(2)促进过渡的相关措施
即便是上述过渡性的教育券方案,其实施仍需要有各方面的配套制度。而且,要为深化办学体制改革铺平道路,也需要有相应的前期准备。因此,在实施教育券过渡计划的同时,应以现有的多元办学体制为基础,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以保障教育券政策的顺利实施。具体建议如下:
① 明确界定民办学校的产权关系
我国民办学校经过20几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尤其是缺乏对学校产权关系的明确规定,民办学校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风雨飘摇状态,产权纠纷不断,而且日益突出。民办学校举办者是否享有投入到学校的财产权?学校存续期间,谁对校产处理拥有最终决定权,举办者,董事会还是校长?学校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如何分配,具体怎么把握?这些问题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仍未作出明确规定。
我们认为,在处理民办学校产权归属问题时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谁投入归谁所有,同时确保举办者的剩余索取权。具体而言,应坚持:(a)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属于举办者所有;(b)民办学校中的国有资产部分属于国家所有;(c)民办学校受赠的资产属于受赠对象所有;(d)财产的增值部分归学校举办者共同所有(剩余索取权)。必须明确,不管校产归谁所有,为确保公民个人的教育权益,在学校存续期间,全部校产(不是指办学剩余)归学校管理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能随意撤走。此外,应开放学费的市场定价,推进学校收费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促使“地下教育产业”公开化、规范化,允许民办学校举办者在合法经营的框架下营利。
② 开放并完善公立学校转制
开放公立学校转制包括在公立学校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适度分离,也包括允许私人教育财团接管公立学校,允许学校之间的并购和重组,允许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等,从而在满足社会成员对优质教育需求的前提下,吸纳社会资源以扩大优质教育机会,最大限度地盘活国有教育资产并力图实现增值,使其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当然,为了在转制的过程中避免造成公立学校资产的严重流失,应该通过教育立法和完善制度等途径建立预警机制。
公立学校转制的出发点是建立合理的学校产权制度,然而在当前的强制转制思路中只是培植了一些新的特权学校,这些学校既占了计划体制的好处,又占了市场体制的好处,而其他学校却只能望而兴叹。如果这种特权现象将继续维持下去,或者,我们试图将之永远合法化,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静态僵化的二元、三元或多元体制。因此,对于公立转制学校而言,当前迫切需要解决“断奶”问题。当然,为了确保公立转制学校顺利渡过生存适应期,可以采取逐步减少直至取消其教育特权的稳妥做法。
③ 加快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的立法
根据前面提出的教育券计划,极有可能出现部分学生不能经由市场机制享受到国家必须确保的基本教育服务的情况。举办者也有权根据自身的办学目标和理念,自主选择开设营利性抑或非营利学校。因此,营利性学校和非营利性学校将同时存在。学校在参与教育市场竞争中,究竟是选择作为营利性学校好,还是作为非营利组织更有效率?这取决于举办者自身的偏好:你是积极追求物质的、直接的利益,还是稳妥追求精神的、间接的利益?我们很难在这方面对学校的举办者提出任何有明确导向的实践建议。
但在教育券计划中,无论学校是营利性的还是非营利性的,都将面对无处不在的市场压力。这就是办学者不得不考虑的“社会建构”。因此,国家应加快对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学校的立法,以加强对教育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具体而言:(a)加强对营利性学校的立法,在允许营利性教育机构存在的同时,通过法律规范这类学校的办学行为,防止出现坑害教育消费者的短期办学行为;(b)加强对非营利性学校的立法,既要防范可能造成的地下产业化,也要防范可能存在的政府在基本教育服务供给方面的卸责。
④ 明确界定学校教育的国家标准
可以预见,在教育券计划所营造的教育市场中,教育产品的特殊性以及教育选择的特殊性,将导致较之一般商品市场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因为作为消费者的家长将缺少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来评估教育服务的质和量:一方面因为他们年幼的子女才是服务的直接对象;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产品的性质非常复杂,其质量更难比较和评判。而教育过程作为一种长期过程,以及师生交往所导致的学生对教师的依恋,在教育选择方面都将造成有利于学校控制学生而不是学生选择学校的局面。这样,如何确保教育中的“消费者主权”,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正是在这里迫切需要有国家公共权力的大量介入。为此,必须花大力气明确学校教育的国家标准(不是像现在这样要求学校教育标准化)。这种国家标准不仅应有基本课程设置与内容方面的要求,也应有追加或特色活动安排的制度规范方面的要求,而且都应是一些底线要求。在前一方面,国家必须明确提出基本教育的服务清单、服务品质的基本要求、开设时间的统一要求。在确定基本教育服务时,应切实考虑到学生多方面的学习需求,不能把基本教育服务完全限制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学方面。在后一方面,为了切实保障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追加或特色服务的自主选择权,有必要统一学校的特色活动安排,为学生自由选择预留统一的活动时间,防止学校滥用办学自主权为个人自由选择乃至跨校选择特色教育服务人为设置技术障碍。
⑤ 转变教育行政部门的现行职能
从法理上看,政府对于学校的管理权能,主要有两个渊源:国家主权和国有产权。其中,国家主权确定了政府对学校的一般行政管理和业务监管权力;国有产权则赋予政府对公立学校经费和人事等方面的各项权能。由此,形成了政府与学校之间在行政、民事和专业等方面复杂的法律关系。所以,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实现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能转变,关键在于明确学校举办者的举办职能、学校办学者的办学职能和政府的管理职能之间的区分,从而放松对教育的行政管制。
我们认为,必须改变以往政府包揽办学的局面,真正做到政校分离,使之摆脱现存的外部科层体制的约束,鼓励和扶持学校的自主发展和公平竞争,使学校教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真正形成持续发展能力。教育行政部门应坚决摒弃行政至上主义,尤其要从人事调配、经费资助、利益分配、项目审批、考试选拔、评优评先等活动中退出,实现管理职能的根本转变。其既是操作者又是管理者的双重身份,如果在改革初期难以避免的话,也不应该长期存在。应使学校逐步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独立法人实体,依法享有办学自主权以及作为其物质基础的法人财产权。对于学校的自主管理活动,教育行政部门只能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而不能对进行非法直接干预。当然,在贫困地区或学生严重流失地区,为那些依然留守的学生提供基本教育服务,也是政府不容推卸的教育责任。
(3)向全面的教育券计划的过渡程序
现在我们来考虑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教育券的改革实践在各地都取得了成功,或者即便没有完全取得成功,但人们对教育券的认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个更为完善的教育券计划很有可能为公众所接受,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向全面的教育券计划的过渡?我们认为,应由国家立法机关在全国范围对更为完备的教育券计划进行审议,通过后交由中央政府在全国推行。由于教育券计划本身涉及教育行政部门的自我转型,这时再让教育行政部门主持制度设计将十分有害,对这一点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主要参考文献
1.高新建.不均等的学习机会与学校选择权.http://www.epa.ncnu.edu.tw/forum.htm.
2.顾一冰.教育券的背后[N].南方周末,2002.12.29.
3.黄显华、钟宇平.学校私营化——理论、效果与抉择[M].香港:小岛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8.
4.季苹.美国公立学校的发展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教育券,能否洋为“中用”?[N].中国教育报.2002.10.20(4)
6.靳希斌.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教育改革[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7.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8.康永久.现代学校双轨体制的代价[J].上海教育科研,2002(8).
9.劳凯声.面临挑战的教育公益性[J].教育研究,2003(2).
10.刘军宁等.市场逻辑和国家观念[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11.刘万永.民办教育促进法案未付表决:能否取得“合理回报”是争辩焦点[N].中国青年报.2002.10.29(5).
12.柳昌林.考前“飞”过来,考后又“飞”走[N].广州日报.2003.1.31(A4).
13.美.D•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14.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司部门的伙伴关系[M].周志忍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5.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6.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张瑞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7.美.伊万•伊利奇.非学校化社会[M].吴康宁.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民国83).
18.秦梦群.教育券政策走向之分析研究.http://www.epa.ncnu.edu.tw/forum.htm.
19.日.藤田英典.走出教育改革的误区[M].张琼华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0.苏力等.规制与发展——第三部门的法律环境[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1.徐冬青.转制学校需要“断奶”[J].教育评论.2002(4).
22.薛兆丰.科教应该商业化[N].http://www.stevenxue.com/st_123.htm.
23.余新.九十年代美国公立学校私营化——教育市场化问题的研究个案[J].比较教育研究.1998(3).
24.袁连生.论教育的产品属性、学校的市场化运作及教育市场化[J].教育与经济.2003(1).
25.袁振国.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6.曾荣光.民族教育和公民权责教育之间:过渡期香港公民教育的议论[J].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报.1995.23(2).
27.曾晓洁.弥尔顿•弗里德曼“教育凭证”思想浅析[J].比较教育研究,1998(3).
28.张民选.转制学校:事实、成因与前景.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一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9.赵中建.从转制学校看中国学校体制变革.丁钢.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第一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30.钟玉明.公办名校转制:谁得益,谁受损[J].人民日报•华南新闻.2002.08.26(4).
附:教育券计划的理论与实践
(一)教育券计划的理论模式
20世纪60年代末,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在美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随之在部分学区实施。70年代,学者发现教育券计划的成功与否与计划的具体内容或模式有直接关系,从而促成对教育券模式的研究。在总结美国学者对教育券模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学者秦梦群提出了四种教育券模式(如下表):
美国自由市场导向的教育券模式
提倡者
教育券面额 准许学校索取教育券面额不足之处
学生交通问题
入学方式 是否允许私立学校加入
是否实际实施
Friedman
(1962) 面额固定(约等于公立学校学生单位成本)
可以追加 政府不一定要提供
学校决定
同意 未曾在美国境内实施,1980年在智利施行
Sizer & Whitten
(1968) 给低收入者较多金额
可以追加 政府一定要提供 可采抽签方式
同意
未曾施行
Coons & Sugarman
(1970) 面额之决定取决于年级之高低、学区生活水准、特殊需求等因素
学校自行决定
政府一定要提供
可采抽签方式
允许宗教学校加入
未曾施行
Jencks
(1970) 接纳弱势学
生,其入学可额外获得补助
不索取追加额
政府一定要提供
可采抽签方式
允许宗教学校加入 于1972年加州Alum Rock试行五年,但私校并未加入
我国学者冯晓霞进一步将其提炼为两种模式:一种是“无排富性”模式,也称「无管制市场模式」(Unregulated Market Model),即给所有适龄儿童等面值的教育券,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不足部分自己支付,以促成自由的教育市场。弗里德曼的教育券理论即属于这一模式。另一种是“排富性”模式,也称「管制市场模式」(Regulated Market Model),这种模式认为前一种模式不能真正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主张只给低收入者或有特殊需要的家庭以特殊的补助。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的理论属于这一模式。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学生家庭状况的不同发给学生不同面额的教育券,使经济资源达到较为公平的分配。这应当也属于“排富性”模式 。
(二)教育券政策在美国及我国台湾的实践
1.教育券在美国的实施
由美国政府资助的教育券实验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此后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到90年代才逐渐展开。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开始正式实施教育券制度。1995年,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克利夫兰市(Cleveland)教育券项目,从1996年起,该市正式推行教育券。1999年春,佛罗里达州议会批准全美第一个全州性的教育券实施计划。目前,美国已有两个城市和一个州正式明确实施由公款资助的“教育券”计划,另外有十个州建立了私人和私立机构资助的“教育券”制度。由于美国教育券实施并无一套统一或标准的模式,各州都根据自身的特性及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券计划,因而有必要作一简要介绍 。
(1)密尔沃基家长选择方案
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Milwaukee)开始正式实施教育券计划——“密尔沃基家长选择方案”。根据这一计划,在密尔沃基公立学校上学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可使用教育券进入市内愿意参与这个方案的私立、非宗教的学校。而对已在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并不被允许参加教育券的计划。而且,教育券实施的对象限于在联邦法定贫穷收入值1.75倍以下的家庭,最初实施的比例定于所有学区学生的1%。换言之,只有贫穷家庭的学生能加入此计划,而且并非有资格者都能领取教育券。教育券之经费来源主要为州所主管的彩券收入,每生所得在1990年为2500美金,1994增至3000美金,与州平均补助学生的金额大致相近。
(2)克里夫兰奖学金计划
1995年俄亥俄州法院通过了克里夫兰(Cleveland)学区用公共税款资助4000名处于危险状况儿童(at-risk children)的“试点方案奖学金项目”,自1995年起,以奖学金之形式来补助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希望能使低收入家庭有选择教育的能力,并因此提升教育水准。根据这一项目,低收入家庭可得到的补助均额为2250美元(约为学费的90%),但条件为家庭收入必须低于联邦所定的贫穷水准20%以下。学生可用所获奖学金选择学区内的公立与私立学校(包括宗教学校),也可以跨区就读,其形式与教育券计划极为类似,只是政府直接发钱给学生而并未印制教育券。
(3)佛罗里达州的“A+”计划
佛罗里达州于1999年正式通过一项被称为“A+”计划的教育券计划。根据该计划,州对学生实行统一的包括读写算等内容在内的综合成绩的标准化考试,根据学校考试成绩的情况,将学校分为A到F不同等级,F为最低等级。如果在四年中有两年,学校大部分学生在考试中失败,则这所学校将得到F。而得到F的学校,在其中就读的未达到州学业标准的学生就有权利申请“机会奖学金”,可领取价值4000美元的教育券,转到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就读。
2.我国台湾实施教育券的现状
我国台湾“教育部”于1995年正式将教育券之列入实施计划中。其中教育券主要分为两种:
(1)幼儿教育券
从2000年9月份起全面发放。
a.发放金额:每张面额五千元,一学期发放一张,不得兑换现金。
b.发放对象:五至六岁、就读私立幼稚园的幼儿。
c.使用方法:家长在私立幼稚园注册的時候,以此教育券抵免学费。
d.教育券形式:以台北市为例,每一幼儿教育券一式三联,第一联家长保存,第二联幼稚园存查,第三联教育局、社会局存查,三联单据由市教育局统一印制。
e.办理方式:以台北市为例,教育局就各行政区内符合资格的幼儿,依幼儿姓名、身份统一编号,将第一、二学期教育券以限时邮寄方式发给家长。各幼稚园应于幼儿注册时,在教育券上加盖幼稚园戳记及园长印章,连同幼儿名册,汇总函报教育局或社会局,由教育局以电汇方式将经费拨入各园账户。
(2)私立高中职教育券
a.发放时间:自2001学年度起。
b.发放对象:采逐年增加一个年级的方式对台湾私立高中职学生发放教育券,计划到2003年度全面发放。但排除下列对象:残障学生或残障人士子女就读减免(补助)学杂费、低收入家庭子女就读减免(补助)学杂费、现役军人子女减免学费、原住民族籍学生助学金等学生。
c.发放金额:每人每学期教育券面额为五千元。
d.实施情况:因政府财政困难,自2001学年度开始,将补助对象局限于就读台湾私立高中、家庭贫穷的学生。受资助的学生名额约占学生总数的20%。与原计划全面发放的初衷大不相同。
台湾有学者对台湾教育券与美国教育券在发放发式、改革目标、补助对象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比较(见下表) :
美国教育券 台湾教育券
发放方式
政府→学生→学校→政府 方式一:由政府印制教育券给学生,入学时抵免学费。
方式二:学生入校后,由学校造册,政府再将现金寄给学生。
改革目标 以改善公立学校品质为目标,1960-70年代明显偏向自由市场导向,1990年代开始则渐有社会正义的色彩。
以发放津贴照顾私校学生为目标,具有社会正义导向。
补助阶段 义务教育(小学至高中) 幼稚教育、高中教育
补助对象 公私立学校学生 私校学生,并有排公与排贫条款
补助方式 凭券制 凭券制或现金制
补助金额 每位学生就读公立学校的单位成本。 未有任何研究之依据,端赖发放政府之财政能力。
补助时间 学生入学前(可因此自由选择学校) 学生入学后(无法选择学校,仅具补助性质)
预期成效 提升教育品质、促使开放及自由竞争市场 补助私校学生,缩短公私立学校的学杂费差距。
(三)围绕教育券计划的利益博弈
教育券作为一项政策实施,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分化与重组,而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公立学校及其教师)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教育券实施的坚决抵制。但更重要的是,围绕教育券理论本身,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仍然同时存在。
赞成教育券(家长选择权)的主要理由:
选择权是穷人和少数民族的年轻人达成教育机会均等的方式。
选择权是家长的权利,可以把孩子从坏学校中解放出来,也可以逃脱公立学校之无宗教意涵的人道主义(secular humanism)。
争取学生和金钱的竞争将会强迫学校改善并更重视绩效。
儿童有不同的学习需要,因此,也需要不同的教学选择。
藉由学校的选择,家长将会更加地投入和奉献于他们子女的教育。
选择权可以促成自愿地消除种族隔离(desegregation),让学生在学校里学到尊重差异。
选择权将会打破教育的独占市场,迫使学校及学区的行政系统更为有效率。
选择权将会导致教师有更高层次的专业精神及专业知能。
批评教育券(家长选择权)的主要理由则包括:
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示竞争可以改善学校或是学生的成就。
最是需要的儿童──有支持性、有能力家长的儿童──很有可能会被遗弃在最差的选择,因而造成不均等的选择。
对社会的利益不利,因为学生可能学不到沟通技能与主动公民的知识、有效地在工作世界中运作、并且无法避免受到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灌输。
除非能提供所需要的交通设施,否则选择权会对低收入的家庭不利;但是,花费在交通车上的金钱倒不如使用在教室内。
私立学校选择将会把把教育经费由已经相当贫困的公立学校吸走。
选择权会把大众需要为公立学校筹措充足财源的注意力转移开。
学校可能无法控制利润的诱惑,因为教育券意味公立教育将成为营利性的事业,可以尽可能地追求利润;学校也可能因之而提供有关效能之表面或不实的资讯与广告,并且需要使用原来可以直接运用于教育的经费与人员。
鼓励学生转学将会破坏提升学校与社区之连结的努力。
教师随时会因为学生的减少而去职或转换学校,不安的工作环境,不利教师身心健全的维持,降低工作满意度与效能。
由于对教育券理论本身存在诸多争议,各国在实施教育券计划时,都不同程度地对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教育券主张,做出了一定的修正,表现为:(1)在政策价值定位上,不再局限于教育市场化的理念,主张学校完全私有化,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而是在主张赋予家长教育权的同时,强调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体现社会正义和教育公平的要求。上述密尔沃基家长选择方案、克里夫兰奖学金计划、我国台湾私立高中职教育券计划及其我国浙江长兴县为低收入家庭学生发放的补助金教育券等,无不体现了这一点。(2)在教育券发放的范围和对象上,倾向在小规模范围内对特定学生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