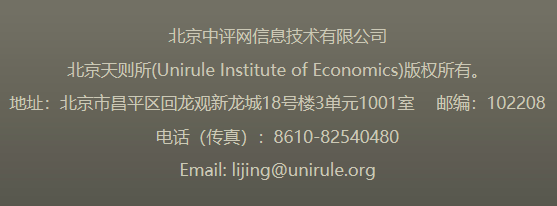能够有机会在这个联邦国家的会议上就教育发表意见令我倍感荣幸。我也十分高兴于各位选择爱丁堡作为本次重要会议的会址。作为此地两校——爱丁堡大学和荷里奥特-瓦特(Heriot-Watt)大学的校友(坦率地说,我只在这两校获得过荣誉学位,但这让我感到距离那里真正的学生非常之近),以及作为爱丁堡皇家学会及其他一些位于这座伟大的城市的协会的一员,我本人与爱丁堡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此我深感骄傲。所以我要以东道主的身份邀请你们来到美丽的爱丁堡及其出色的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很荣幸我是这个群体中流动的一分子,就像一个学院派的吉普塞人一样。但是对于这个欢迎我还要加上我的一份信仰,即我相信没有哪个城市能像亚当•斯密城和大卫•休谟城这两座最早和最大的全民教育的拥护者那样适合召开一次关于“填补教育中的裂隙”的会议的地址了。
为什么填补教育中的裂隙、消除教育机会、入学和成绩面前的巨大不平等是重要的?在众多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原因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公平和安全。HG维尔斯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并没有夸张。在他的《历史的轮廓》一书中,他这样写道:“人类的历史变得越来越像是一场在教育和灾难之间的比赛了。”如果我们允许很大一部分人口游离在教育的轨道之外的状况继续持续下去,那么我们不但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不公正,而且会变得更加不安全。
现在的世界已经比HG维尔斯所处的20世纪初期的世界更加不稳定。事实上,自从可怕的2001年9.11事件之后——以及随之而来的事件——这个世界已经对有形的不安全问题有着相当的认识了。但是人类的不安全感来自多种因素——不光是恐怖主义和暴行。事实上,即便是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死于艾滋病的人要多于那些死于包括发生在纽约的恐怖袭击在内的一系列恐怖事件的人。人类的不安全也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来加剧,而有形的暴行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反对恐怖主义和种族屠杀(在这一点上,教育也能发挥巨大作用,这正是我将要讨论的)固然是重要的,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类不安全及其多种表现的多重性质。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扩大和提高基础教育的覆盖面与效率几乎可以强有力地预防任何一种不安全的发生。简要思考一下消除教育中的偏差和疏漏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低人类的不安全的不同方式,也是大有助益的。
最基本的问题涉及到文盲和科学盲本身就是不安全的形式这一基本事实。不能读写、计算或者交流是一个巨大的丧失(deprivation)。极端的不安全的例子是这种丧失的确定存在而且没有任何机会避免这一命运。成功的学校教育的首要贡献是直接降低了这种缺失的可能性——这种极端的不安全——它能持续地摧毁全球人口中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而不仅仅这个联邦国家。
基础教育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改变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最穷困的家庭也愿意接受这一点。从我个人的角度说,教育的重要性能这么容易地被最穷困和最缺乏基本生活物资的家庭所认可,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妙了。这得益于我们现在在印度做的一些关于初等教育的研究(通过Pratichi信托基金——从1998年我用我的诺贝尔奖奖金在印度和孟加拉国特别设立的一个旨在推动基础教育和性别平等的信托基金)。随着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推出,我们发现即便是最穷困和不济的家庭也是多么渴望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一个受教育的机会,让儿女们不再带着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可怕的障碍而健康成长。
事实上,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我们发现,对于送孩子——上学无论是女儿还是儿子,只要在他们的社区确实存在能负担得起的、高效而安全的教育机会,没有哪个父母会有半点不情愿。当然,父母的教育梦的塑造还存在着许多障碍。家庭的经济状况常常让他们很难把孩子送去学校,尤其是在需要支付教育费用的情况下。
负担不起的问题必须坚决在联邦国内——事实上是全世界——得到消除。我当然知道一些市场机制的支持者希望把教育费的问题交给市场的力量去解决。但是考虑到为所有儿童提供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这一社会责任,这必然是一个错误。事实上,在两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了对权力和市场机制的经典分析的亚当•斯密坐在科克卡尔迪(Kirkcaldy,离这不远)雄辩地写到,为何把这个交给市场是错误的:
只需要很小的一个开支,公众就可以推动、鼓励、甚至能强迫全体人类都接受那些必要的教育。
还有其他的障碍。有时候学校的老师非常少(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小学都只有一个老师),家长总是担心孩子的安全,特别是女孩子的安全(特别是在找不到老师的情况下,这似乎在许多穷国都时常发生)。因而,做父母常常不愿意送孩子上学就有了合理的理由,这些裂隙也需要强调。
另外,很穷的家庭往往要依赖每一个家庭成员、甚至是孩子的劳动力来贡献收入,这往往会与教育需求形成竞争。这种不幸的事虽然是由于穷困而引起的,也必须通过监管及让大家更加明白受教育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得到消除。这就提出了第二个关于理解教育在消除人类的不安全中的贡献的问题。基础教育对于帮助人们就业和获得高薪职位至关重要。这种经济上的关联一直在上演,对于一个迅速全球化的、讲究质量控制和规范生产的世界而言尤为重要。
利用全球商业来消除贫困的所有例子都是广泛地受益于基础教育的发展。例如,日本在19世纪中期对教育的重要性就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1872年(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颁布的《基本教育大纲》,表达了公众对教育的重视,它明确提出要确保“社区里没有文盲家庭,家庭里没有文盲成员”。由此——随着教育裂隙的愈合——日本经济进入了历史上快速发展的辉煌时期。到1910年,至少对于少年儿童而言,日本实现了教育普及化,到1913年,虽然经济上仍比英国或美国弱,但是日本出版的书却比英国多,比美国多一倍。对教育的关注和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性质和速度。
后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期,南韩、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遵照日本的发展轨迹,十分坚定的集中在教育的普及上。如果人们无法读写,或者根据要求或指导进行生产,或者实施质量控制,那么就无法广泛地参与到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中。
第三,如果人们都是文盲,他们理解和运用其法定权利的能力就很有限,教育上的缺陷还会导致其他的权利的被剥夺。事实上,这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一辈子的问题,由于不会读书,看不到自己的权利,也不知该如何运用,这些人的权利被实际地剥夺了。教育上的裂隙很显然与阶层有关联。
教育还与性别有关,因为教育是女性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没有文化,女性常常被剥夺她们所应该享受的权利。不会读书写字是那些下层社会的女性的极大的障碍,因为这会让她们无法运用哪怕是那些相当有限的合法权利(比如,拥有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权利,对不公正审判或不公正待遇进行申诉的权利)。规则手册上往往都规定了很多合法权利,但是受损害的一方往往因为不会读书写字而无法使用这些手册。因此,教育上的裂隙可能使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找不到救济手段和途径而直接导致不安全。
第四,没有文化还会削弱受压迫者参与政治活动和表达其需要的能力,从而压抑政治上的机遇。这会直接影响个人的安全,因为在政治上没有话语权会严重地削弱影响力,增加了那些被排挤在教育之外的人获得不公正待遇的可能性。
第五,基本教育在应对一般的健康问题或者是流行病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们很容易就能知道专业的健康教育(例如,传染病传播的途径和如何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但是即便是一般教育也能扩大一个人的思考的视野,催生社会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于应对流行病疫情问题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一些研究表明,一般性的学校教育对于健康的影响要比专业的健康教育本身的影响大。
第六,近年来经验性的工作清晰地显示出,对妇女的文化程度和家庭内外决策的有效参与对于妇女的福利的尊重和重视有着多大的影响。随着妇女逐渐掌握权利,而这其中文化教育是一个基本的要素,即便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与男性相比的残存的劣势(这导致了数千万“丢失了的妇女” 这一可怕的现象)似乎大大地减少了——可能已经没有了。
还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人口的出生率随着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而大幅度降低。这并不奇怪,因为生命总是被不断的生育所搅乱,而生儿育女的往往都是年轻的妇女,任何有助于增强其决策能力以及引起社会关注她们的利益的东西一般而言都有助于防止过度频繁地生育。例如,一个针对印度不同地区的比较性研究清楚地表明,妇女的教育和就业是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最为重要的两种影响力。在这项广泛的研究当中,女性教育和就业是解释整个印度三百多个地区不同的人口出生率的具有显著性统计特征的唯一变量。在理解地区内部的差别时,例如印度的克拉拉邦只有1.7的人口出生率(可以粗略地认为每一对夫妇平均有1.7个孩子),许多其他地区的夫妇则平均有四个以上的孩子,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提供了最有效的解释。
还有很多证据证明,妇女的教育和文化程度可能会降低儿童的死亡率。妇女的基本教育与妇女的力量(及其广泛的影响)之间的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说明了为什么教育中的性别差异会产生那么严重的社会苦果。
到目前为止我关注的是教育的通路、入学和成绩这些让人与人如此不同的因素。但这个时候也是讨论一下一个很不同的——存在与学校课程设置上的——小差距。课程的本质当然与那些能够推动当今社会的参与的技术有关。但是决不仅止于这些,因为学校教育能深刻地影响一个人的身份和我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
最近这个问题在信奉正统派基督教的宗教学校中引起关注,有必要注意一下没有文化和偏执的教育对于狭窄视野的催化作用,尤其是从儿童的角度。认识到儿童受教育所需的公共设施的匮乏会极大地有助于增加由政客开设的宗教学校的名声和受欢迎程度。
事实上,教育的性质与世界的和平紧密相关。近来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观点——所谓的“文化冲击”(塞穆尔•亨廷顿特别支持这个观点)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有点理论化的观点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分水岭并不是认为“撞击不可避免”(这也是,但排在后面)这个愚蠢的理论,而是一种同样浅薄的先验偏见,用一个维度来看待人类,认为人仅仅属于这种或那种文化群体的一员(绝大多数是以宗教信仰来界定的),而忽略了人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和参与。
这里有两个错误。第一,这种分类是很拙劣的。例如,虽然有1.3亿的穆斯林(比整个英国和法国的人口之和还多),印度还是被归于印度教(Hindu)文明之列,印度的穆斯林数量要比世界上大多数所谓的“穆斯林国家”的数量还要多。亨廷顿的分类只能让那些印度教宗派主义者感到高兴。
第二个错误是假设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会恰当而充分地决定一个人的身份。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份由许多不同的要素构成,涉及国籍、语言、区位、阶层、职业、历史、政治信仰等等。一个位于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不仅仅是一个穆斯林,他还是一个孟加拉人,很可能为他的孟加拉文学和其他的文化成就而感到骄傲。同样地,一个与今天的每一个阿拉伯儿童紧密相关的阿拉伯世界的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伊斯兰教的成就(虽然这很重要),还包含了在数学、科学和文学等领域的长期的灿烂文明。现在当一个皇家学院的科学家使用代数(algorithm)的时候,他/她都无意中颂扬了9世纪阿拉伯数学家艾尔•克瓦利兹米(Al-khwarizmi),运算法则的鼻祖(“代数学”一词就是从他的《Al Jabr wa-al-Muqabilah》一书中来的)的伟大的数学贡献。
仅仅用以宗教为基础的文化分类标准来界定人们的做法本身就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不安全,因为这个看法中的人都有着简单的归属,例如,这个人属于“穆斯林的世界”,那个人属于“西方世界”,或者“印度世界”,或者“佛教世界”,等等。把除了宗教之外的所有标准都忽略掉,用这样的办法来划分人就好比是把人们都放入潜在好战营一样危险。我个人相信即便是英国政府没有限制以信仰为基础的国立学校而是任由其扩大规模,没有为那些先于基督徒而存在的信仰者建诸如穆斯林学校,印度学校和印度锡克学校,特别是当新的宗教学校没有为孩子们提供足够的机会来培养理性的选择和决定他们身份的这些不同构成因素(分别与他们的语言、文学、宗教、民族、文化历史、科学兴趣等等)应当引起他们怎样的注意,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不仅需要讨论一下我们人类共性的重要性,而且还应当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不同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我们必须运用我们的理性来决定如何看待我们自己。
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和教区的课程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扩大而不是缩小理性的范围,这一点毫不夸张。莎士比亚谈到“一个人生来就是伟大的,一些人实现了伟大成就,还有的人被伟大所左右”的事实。在对孩子的教育中,我们必须确保不把卑微强加到孩子们头上。
在这样一个广泛的方法背后,联邦国家的观点有几分哲学意味。作为联邦国家的元首,英国女王在1953年加冕后不久就清楚而坚定的宣布了她的基本看法:
联邦国家•••是一个建立在人类的精神最高境界的全新的概念:友好,忠诚,对自由和和平的向往。
在对友好和忠诚的推动中,在对自由和和平义务的保障上。基本教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要求教育设施要惠及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儿童要接受来自各种不同背景和视角的观点,并应当鼓励他们为自己理性地思考。
基础教育不仅仅是一种为了发展技能(虽然这个也很重要)的培训安排,它还是一种对世界的性质的认知,对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解,对自由和理性及友好的重要性的认识。理解这一点——以及这种视野——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