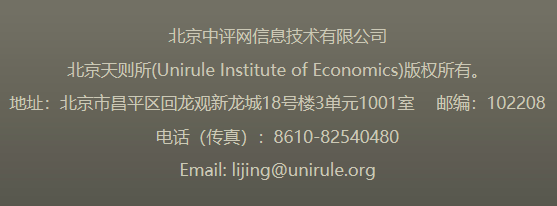谢谢会议的安排者。我们这个单元成了人民大学专场了,两位发言人都是人民大学的,我也是人民大学出来的,当时是上历史系。
坦率的说,我要把握他们两位所讲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听下来之后,觉得吴思先生的讨论和高教授的讨论,其学术进路其实有一些区别。我听吴思先生的这些研究,大概是要把文明的世界还原到自然状态,然后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规则和制度如何形成。可能有点像霍布斯所做的工作。当然,他大量借鉴了历史故事。尤其触目惊心的是,他把生命作为交换对象。我们经济学还是在文明层面讨论问题的,所以交换的都是商品、资本这些东西,但吴思教授要我们回到一个最自然的状态中。当人们要交换生命,经济学的逻辑还有没有效率?当然是有效率的,霍布斯也许就是现代经济学基本预设的创始人。
高教授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历史学研究,而又有理论的视野。他透过对明清时代经济史的讨论,让我们重新思考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结论。
今天,会议组织者之所以安排这两位发言,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是历史学家,他们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中国事实。当然,刚才,林毅夫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中国事实。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从古代一直到当下的中国事实链条。
我想,中国事实可能就是我们中国学人的“后发优势”。若干年前,林毅夫先生和杨小凯先生争论过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我曾把这个论题转换到知识的问题上,我说,我们中国学者会陷入到一个知识上的后发劣势中,就像刚才林毅夫先生所讲,我们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发展问题。这就是后发劣势。今天,中国学生去哈佛,去MIT,学的肯定都是最先进的理论,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理论对中国而言,很可能是屠龙之计,解决不了中国问题,反而伤害我们自己。
因此,当学习西方知识时,中国人需要有一个反思的意识,我们必须警觉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知识上的劣势地位转变到一个优势地位上。这个后发优势是什么?我们就在事实和理论之间。
西方人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论,一套非常完备的分析的工具,它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事实,不管是历史的事实还是当下的事实。但是,这套理论真正有效的时候,恰恰是我们意识到它在中国的有限性的时候,意识到它的局限性的时候。我们若有反思的意识,我们就有可能丰富这套理论,有可能用中国事实来丰富这套理论。
为此,我们恐怕不能不说,西方理论只是一套地方性知识,它不是普遍的知识,这个普遍的知识有待于中国人参与构建。就像刚才陈平老师说的,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在现有的这套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只有半个世界参与了,另外一半世界没有参与,那就是中国。也许,我们中国人发现自己的故事,思考自己的故事,在事实和理论之间持续互动,推动理论的生长,才会形成一个真正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有能力普遍地解释人的行为。现在这套理论也许能够解释西方在过去500年现代发展转型的过程,能不能解释中国?这真的是需要我们有所保留,不是毫无保留的接受它。
我们不能不如此,因为,我上面说了,中国是一个世界。这是我们思考所有问题的出发点。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舞台,在中国,不管是政治、文化、经济的故事,它有一个舞台。我们可能需要讨论,这个舞台和西方人的理论中所预设的舞台是不是一样?我这些年一直在读《尚书》,我发现,其实中国人从一开始就是在思考协和万邦的问题,就是天下治理的问题。而西方理论,比如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他们讨论的都是城邦的治理问题,那都是点状的城邦。其实,现代民主制度、现代民主理论都是讨论一个点状城邦、一个只有五千公民的城邦如何治理。可是,中国一开始就是100万人,而且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的乡村地区。
这就是中国最重要的特点,由此就决定了它的观念,它的信念,它的价值,跟西方有不同之处。我没有说它完全不同,但一定会有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民主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思考中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根本不可能。在古代那样一个环境,它就不可能。民主在城邦是有可能的,但是在超大规模的文明与政治的共同体无法做到。相反,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走了共和之路。而对共和来说,“代表”的问题是核心问题。于是我们看到,后世的制度,不管是汉代的察举还是宋明的科举,都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因为,中国的规模太大了,没有办法像一个城市那样把所有公民召集起来通过民主方式解决公共问题。
我最近看考古学材料,在看费孝通先生,也在看李伯重的经济史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事实,中国在解决自身问题中探索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规则、制度的体系,与西方有某些不同之处。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今天上午史正富先生的说法,我们要有主体性意识,我想,这是知识和理论的主体性意识。
但我马上要补充一句:我们也要有普遍主义的情怀。我们讨论中国自身发展历程,把中国故事讲清楚,目的并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很特殊,而是要证明,人很复杂。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理解普遍的人。我设想,随着知识的积累,中国学者贯通西方的地方性知识和中国的地方性知识,发展出一个涵摄了现有西方理论、而更为普遍的关于人的科学。这是我的白日梦吗?
[ 秋风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年6月20日
中评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