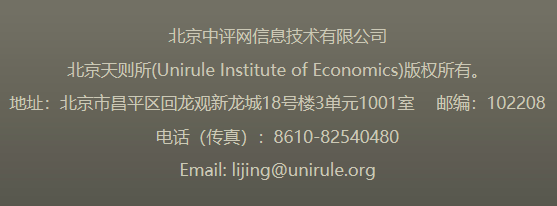我以为今天这个会是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更好地进行研究上的创新,而不是来讲自己做了什么创新。但我发现到目前为止,大家讲的都是自己的创新性研究。而我将从怎样更好地进行研究上的创新来谈。
我们这个会议叫做“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讨论创新研讨会”,所以,我想围绕为什么需要强调中国问题研究?怎样从中国问题研究产生理论创新来展开讨论。我觉得这里面有以下几对关系需要讲清楚,不然可能产生很多认识误区。中国研究跟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是什么关系?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重视,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又是什么关系?如果时间允许,我也将介绍两项自己在研究方面尝试进行的一些创新工作。
先谈谈中国研究和理论创新是什么关系?这个会议是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中国经济学”这个说法有时候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误以为是中国的经济学。我个人不主张这样理解,经济学就是经济学,没有中国的经济学,美国的经济学,经济学就是用科学的工具、方法,进行逻辑的推理,发现规律,解释现象。当然,我觉得中国经济学这个说法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源于中国的素材、事实,可以开展很多创新性的经济学研究,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而我们这个会议所强调的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恰恰应该是基于中国的素材、中国的事实来提出创新的理论与洞见,或是对相关的理论进行检验,发现新的规律等等。
我个人从自己研究经历出发,认为我们只要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就会有很多东西值得研究,而且这里面是有大量的进行创新的空间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有其独特性,地理上的、制度上的、文化上的,这些独特性都是我们创新的源泉。以地理为例,中国是大国,而且地区之间异质性非常大,包括自然的、发展阶段的都不一样。比如我们讲到环境治理问题,有人说环境治理国外可能花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环境就彻底治理好了。但是,我觉得中国恐怕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当北京想搞环境治理,上海想搞环境治理的时候,内地还要GDP,内地对环境不是那么在意,而环境问题有严重的地区之间的负外部性。所以,我觉得在大国的背景下讨论环境治理会更为复杂,但这也恰恰是我们进行创新的源泉,这也是最近我与合作者在推进的研究工作之一,不久就能够和大家分享这方面更多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的研究将说明,恰恰就是因为中国这个大国在地理与发展特征上和人家不一样,才可能使我们对于治理环境的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又比如说,新经济地理学有一个关于“中心-外围”的理论,但是实证上面一直没有很好检验,我们曾做过一个实证的工作来检验这个中心-外围模式。为什么中国会更适于检验这一理论呢?因为独特的地理。第一,中国足够大,而中心-外围理论是需要有一个大的空间尺度来体现其机制的。第二,中国仅在东部有大港口,而出海口接近国际市场,这就是理论模型中的“中心”,内地则是“外围”。美国虽然也足够大,但是两面靠海,中心到外围的空间尺度可能就不够了。
中国的制度同样有其独特性,我们有大量积极的干预政策,比如产业政策就被积极广泛地实施。但是产业政策的效果到底怎样?这在理论上一直是有争论的。中国的产业政策给我们一个检验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一个制度实验场。包括对于产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回答。
中国的文化同样独特。经济学研究里面有一个关于社会网络在市场化中的作用到底怎样的研究话题。例如,人际关系或关系网络是不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就变得不重要了?其实不一定,很有可能是社会关系嵌入到市场机制里面,帮助个人攫取利益。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所以我们曾考察过关系在个人是否进入高收入行业中起到什么作用。源自于中国丰富的素材,我们也能够对现有理论进行再检验,如果里发现现有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现象,你就可以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这就是提出新理论的可能性,是创新的源泉。
我要说的第二对关系就是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我觉得有一种倾向,好象大家比较重视理论研究,不是那么强调实证研究。比如到目前为止大家的发言,昨天包括今天上午,你们发现没有,基本上都是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应该是基于对中国事实素材的认识来提出新的理论,这两个东西是缺一不可。就是说你要检验理论,要发现新规律,你要有事实的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你得知道,这是需要有实证研究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当我们试图提出新理论的时候,首先得知道原有的理论是什么,这个参照系是什么?不能参照系都没有搞清楚,你就提出来一个新的理论,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样学科就没有进步了,没有传承了。即便我们不是看计量研究,只是看案例,我们也要遵循科学精神,把这个事实说清楚,而不是像记者式愤青一样,这个说说,那个扯扯,然后凭空抛出所谓的创新理论,这离我心目中认为的经济学的创新应该的模式相差很远了。
正是因为中国有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很多政策又在不同时点上推行,政策的力度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外生性的制度变化在时间、空间和程度上都有差异,这给了我们大量的机会去做一些准自然实验的经济学分析,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比如最近我们有一项研想回答出口加工区的政策效果到底怎样?我们发现,如果所扶持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一出口鼓励政策就能显著促进出口,否则,其效果就不显著。这项实证研究本身也说明,有了这样一个关于比较优势的理论指导,就可以帮助我们验证这样的理论。
另外我要讲的就是国别研究和一般贡献的关系。一般人认为好象中国研究就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好象要低一个档次似的。其实跨国研究,国别研究都非常有必要,但是做国别研究,你不能只说我就是做这个国家的研究,你要通过这个国家的具体素材找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我们需要把国和国进行比较,因为国和国的制度环境不一样,这才能更好地检验现有的理论,因为现有的理论往往是在某一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得出的。所以,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一般化可能并不是有益的”,就是认为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想法可能并不正确,“除非得出这种一般化的研究考察了在不同的制度框架内这些活动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结合中国的情况,因为中国的地理、文化、制度和别人不一样,把现有的理论拿过来的时候,特别需要在中国检验一下,看看这个规律在中国制度框架下是不是成立。从这个角度讲,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研究都可能会很有价值。比如日本学者的一项研究发现,西方企业内部成功实施的对销售人员的计件激励方式在日本却没有改善员工的绩效。为什么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恰恰是这一理论并没有考虑企业内部的集体主义文化,而这在日本却极为重要。所以,在一个不同的文化下面可以产生很好的激励效果的政策,换一个环境可能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拓展原有的理论了,这个就是理论创新的一种途径。
我很想讲的最后一对关系就是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现在政策研究越来越被强调,各个地方都在搞智库,我所在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是上海市高校的智库。目前,大家对政策研究都是越来越为重视。但是,现在可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比如,有时我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年轻人就是要多发论文,评了教授那么压力了,就可以多做点政策研究。也有时,不同的学者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你是做政策研究的,他是做学术研究的。我并不认可以上的这些说法,在我看来,政策研究和学术研究没有明显的界限。那么,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什么才是好的政策研究呢?在我看来,好的政策研究,就是“有明确政策指向的学术研究”。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其实是一回事。特别是对于广为建设的这个智库,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应该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就是你所从事的研究项目要有明确的应用性,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从实践中产生,其答案又对实践有很强的指导价值。当然,既然强调仍然是学术研究,就要有科学性,但科学性难道不也是政策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吗?所以像茅老(茅予轼先生)讲的公租房不要设单独卫生间的说法,我在复旦上《信息经济学》课时就会拿来跟学生讨论。我问学生,很多人反对这个观点,你们怎么想?其实我想引导学生们明白的道理就是,这个说法的背后是机制设计的理念:你只有把廉租房的质量向下扭曲以后,穷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房子,这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这种看起来的不合理却是最优的。反过来,如果你把兼租房造得和市场上的房子差不多标准,那么真正的穷人恐怕就难以分享了。这就是对政策的科学性的考虑。当然,我觉得智库还应该有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独立性和前瞻性。所以,智库不应该只回答政府提出的问题,也不只是解决眼下政府碰到的困难。这样你才既可以有独立性,还可以有超前性。我们刚刚做了一项关于职业教育回报的研究,我之前并没有专门关注教育的回报,为什么突然开展这项工作呢?因为我发现,不论是中国目前所强调的产业升级,还是城市化过程中各种成本的不断提高,都会使得以前那种靠廉价劳动力而推动的制造业增长模式不能长期维持了,我们需要有人力资本的技能提升。但是,我们的农民工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怎么办?靠高等教育吗?异地高考的推进很难,大学生自己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相反,职业教育的人才就业率却要高得多。但是,沿海地区在职业教育上也仍然存在一些与户籍相联系制度性壁垒。那么,职业教育是否急需打破户籍门槛的限制呢?这取决于农民工在不同地区接受职业教育后,其人力资本的回报有无显著差异。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在东部地区接受教育的质量高于在中西部地区,所以职业教育需要向农民工放开户籍限制,让他们在东部发达地区也能平等的接受职业教育。这也符合发达地区自身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加速产业升级的要求。我以这个研究为例,想说明的是,这是一项学术研究,但同时也能够为政策提供有价值的指引,这正是我所认为的学者以智库研究人同的身份应该做,也能够做好的事。
[ 陈钊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5月6-7日「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标题为编者所加 ]
2014年6月20日
中评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