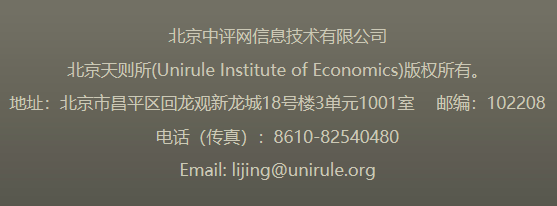华生先生2013年年底指出,中国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存在“六大认识误区”。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研究,我们认为华先生的观点虽然犀利,但总体上很难成立,所以本课题组曾撰写《土地制度改革误区何在?》(FT中文网,2014年2月11日)跟华先生商榷。华先生虽然不同意我们的商榷意见,但却认为这是“学术研究中切磋观点、搞清问题的好形式”,所以又撰写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焦点分歧》一文回复我们的商榷意见。
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和地看待来自其他人的商榷意见。所以,在这一点上,本课题的所有成员都是非常尊敬华先生的。不过,正如华先生所说的那样,土地制度改革具有高度复杂性和挑战性,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依然存在很多分歧。所以,为了进一步理清土地制度改革领域所存在的一些困惑和分析,我们认为有必要就华先生的回复意见进行再次商榷,并以此求教于方家。
“土地开发权与所有权分离”是偷换概念
华先生认为“土地开发权是解开土地迷局钥匙”,而他与本课题组之间的首要(也是最重要的)分歧是“土地的开发建筑是产权人的私权利还是社会的公权力”。虽然这个表述不是很严谨(社会是没有公权力的,只有政府或者政府授权的组织才有这项权力),但这一个总结确实指明了我们之间的分歧在于“如何认识土地开发权的来源和归属”问题。
在华先生看来,早期农业社会中,在乡村土地上盖房子确实曾是所有者的自然权利,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如果将土地的开发建筑仍然界定为产权人的权利,会造成巨大的社会负外部性,同时由于这种外部性影响的广泛分散和相互叠加,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市场失灵。因此,他提出,至少从上个世纪初开始,西方各国都通过立法形式将土地开发建筑的权利与土地所有权分离。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在一次内部讨论会上,华先生认为本课题组对于土地权利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农业时代,而他的见解则立足于工业时代。
我们不能同意华先生的上述意见。在华先生看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西方各国都通过立法形式将土地开发建筑的权利与土地所有权分离。那么,什么叫做“土地开发权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呢?既然在早期农业时代,在土地上搞开发建设是土地所有者的权利,那到了工业时代以后,土地开发权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以后,跑到哪里去了呢?华先生认为,与土地所有权“分离”以后,土地开发权经由国家的规划管制变成了“国家所有”,然后由国家按照分区规划等规划管制措施再“特许”给公民和其他土地权利人。
这种论证方式貌似环环相扣,天衣无缝,但实际上是在“国家所有”与“国有化”之间进行的“狸猫换太子游戏”。且问,国家的规划管制是如何将土地的开发权变成了国家所有的呢?华先生没有对此进行论证,但实际上这个问题才是他所说的“解开迷局的钥匙”。
其实,如果按照华先生的逻辑,他的论证应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才是完整的:(1)在农业时代,土地开发权是属于土地所有权人的;(2)到了工业时代,土地开发权被国家无偿国有化了,土地所有权人仅仅剩下按照现有用途使用土地的权利;(3)如果土地所有权人想要改变土地的用途,其必须向国家特许了;(4)如果没有获得国家的批准,那么在土地征收时,土地所有权人只能依照原用途为基础进行补偿。所以,华先生的真实意思是“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国家通过规划将土地所有权人的土地开发权国有化了”。
所谓“国有化”,就是把不属于国家的财产变为国家所有。那么,国家依据何种理由可以将非国有财产“国有化”呢?通常来说,有“没收”和“征收”两种方式。公民如果犯了叛国罪或者其他需要剥夺财产的罪行,没收其相关财产无可非议,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形,那国家就只能有偿征收而不能无偿没收其财产了。根据世界法治国家的通例,国家要征收非国有财产就必须遵守“公共利益+正当程序+公正补偿”这三大要件。我国宪法虽然没有规定得如此完备,但第10条第3款和第13条第3款却也有关于“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土地和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
那么且问,当1998年《土地管理法》原则上禁止集体土地进行建设开发,并因此剥夺集体土地大部分开发权时,是否给过集体土地权利人补偿呢?答案是否定的。那如何来看待《土地管理法》的这一规定呢?我们认为,除了认定《土地管理法》违反宪法以外,很难再有其他的解释方案,除非我们认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人都是应该被“没收财产的罪犯”。
英国“土地开发权国有化”的教训
英国被认为是“土地开发权制度”建立的母国,这一点并不存疑。1947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决意要执行激进的“土地开发权国有化”战略,将全国私有土地的开发权全部“国有化”,然后由政府代表国家享有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不过,作为一个民主法治国家,英国的“国有化”与中国1998年《土地管理法》的做法并不完全一样。因为其所进行的“土地开发权国有化”并不是无偿的,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专门建立了一个金额为3亿英镑的基金来补偿土地权利人的损失,并打算在1954年之前对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进行补偿。
不过,英国的“土地开发权国有化”战略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反而给公民权利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伤害:由于开发土地的利润完全被政府拿走,人们丧失了开发土地的动机;无人愿意开发土地,土地市场因此萎缩;政府力图取代市场成为城市住房和城市更新的供应主体,但“重建英国”的工作却进展缓慢。(关于这段历史可以参见巴里•卡林沃思,文森特•纳丁所著的《英国城乡规划(第14版)》的梳理)。 所以,短短的6年之后(即1953年),英国政府就通过修改城乡规划法废除了“中央土地委员会”和“100%土地开发费”这两项激进措施。1959年,英国又将“公平的市场价格”作为强制收购的补偿标准,从而保障被征收人享有“按照市场价格获得公平补偿”的权利。
1964年,英国工党再次执政。为了不过分损害公民的土地权利和民众开发土地的热情,工党政府开始主张通过征税来实现“土地增值的社会返还”这一目标。1965年,工党政府主导的议会通过了该年度的财政法案,该部法律允许政府开征资本利得税,这其中就包括对公民出售或者出租土地的增值收入征收税款。
1967年,在工党的主导下,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土地委员会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将设立专门的土地委员会来负责征收地产增值税,最初的税率为40%,后来涨到了45%- 50%。不过,1970年政党轮替以后,保守党政府认为“在自由社会中没有土地委员会存在的位置”。该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所依据的法案于1971年被废止,“地产增值税”只征收了三年左右。
如果将英国上述频繁的制度变迁完全归结为党争是不客观的。英国保守党并不完全反对工党“将土地增值返还给社会”的理念。比如,1973年12月,隶属于保守党的财政大臣安东尼•巴伯(Anthony Barber)就曾提议,对公民处分土地和房屋的实质性收入所得征收开发利得税(Development Gains Tax),但议会还未批准该项计划,保守党政府就下台了。1974年重新上台的工党政府部分同意巴伯的方案,但他们认为开发利得税不够彻底,所以主张开设税率为80%的土地开发税取而代之。在工党的主导下,英国议会于1975年先后通过了社区土地法案和土地开发税法案来落实这一计划。不过,1979年大选之后上台的保守党政府并不喜欢土地开发税这一遗产,他们先是调低了该税的税率(从80%降到了60%),后来干脆通过1985年的财政法案取消了这个税种。
此后,英国没有再征收过单一的土地增值税或者地产税,“土地增值的社会返还”这一目标主要是通过土地交易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以及市政税和营业税等分散的税种来实现。在英国,一直有理论家对此表示不满,他们提出将上述相关税收整合为单一土地增值税的各种主张。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些主张并没有被政府采纳。(关于英国这段历史的详细梳理参见程雪阳:《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对于英国的这段历史,华先生在有意者无意间“把教训当作经验”,以为土地开发权国有化是西方社会的常态。然而上述历史表明,英国在1947年确实曾经试图将土地开发权“国有化”,但历史证明,即便是这种“开发权有偿国有化”,也仅仅是一次短命的“制度试错”。如果说这种试错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和教训的话,那也应该是通过开征土地增值税的方式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返还社会”目标更为合理,而不是把“土地开发权国有化”这种教训当作经验来加以发扬。
“建筑不自由”不等于“土地开发权国有化”
有在西方生活经历的人可能会说,华生对于“建筑不自由”的描述是正确的,在很多西方国家,不仅建筑的高度,密度和容积率受到规划的严格管制,而且建筑的外观、颜色乃至室内的格局也是要符合建筑标准的。我们课题组成员也曾在英国、美国和荷兰生活或者游历,所以我们对于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环境保护,耕地保护,开敞空间的维持或者建筑美学的要求),建筑权利应当受到管制这一问题,并无异议。
可是华先生将这种现象总结为“建筑不自由”,并将这种“建筑不自由”解释为“土地开发权与所有权分离”之后,“开发权”和“建筑权”属于国家,那就让我们大跌眼镜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建筑确实不完全是自由的,不能想怎么建就怎么建,但这种“建筑不自由”的解释应该是,政府可以通过分区规划限制土地权利人的土地开发权,但这种限制并不是将土地开发权国有化,更不是说土地开发权就自然而然地归国家所有。
那么政府对土地权利人开发权的限制是否要给予补偿呢?对于这个问题,德国人的回答是“任何财产都负有社会义务”,如果这种“社会义务”应该是普遍的,那是不需要进行补偿的。但如果这种社会义务针对具体的个人或者具体的地块,当事人因此为社会做出了“特别牺牲”,那么就必须给予补偿。美国人的看法大致也差不多,只不过他们是用 “合理限度”理论来解决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在1922年的一个判决中提到,财产权可以受到政府的规制,但如果这种规制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对于特定人造成特别的损害,就需要给予补偿,因为这种基于规制而产生的损害产生了实际征收的效果。而在1988年的Riggs V. Township of Long Beach一案中,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进一步认定,如果政府维持分区规划(Zoning Plan)的惟一目的在于降低该区域土地的价值,进而其可以以较低价格征收相应土地时,根据“实体性正当程序”的原则,政府的这种行为是违宪的。
请注意,我们同样也认为建筑权利或者土地开发权不是绝对自由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跟华先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在我们看来,只要有人类社会,就不会存在绝对的自由。但我们跟华先生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认为,土地开发权虽然可能会受到政府管制,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就不再属于土地权利人了,更不是说规划管制由此竟然成为土地开发权的来源了。
另外,分区规划等规划管制措施只是土地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而且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不能将这种管制方式神化。在我们看来,政府的土地规划管制不可或缺,但其适用的范围和效力是有限的,在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土地利用负外部性问题上,通过市场、习惯法和私法规则(比如相邻权)来解决这些问题,更为有效、更为基础,因此也应当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华先生将我们与他之间的分歧定位为“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观念分歧,实在是过于夸张了。
天则经济研究所“土地制度研究课题组”组长盛洪教授和课题组成员杨俊峰、徐振宇和程雪阳参与了本文稿讨论和修改,文章由程雪阳执笔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