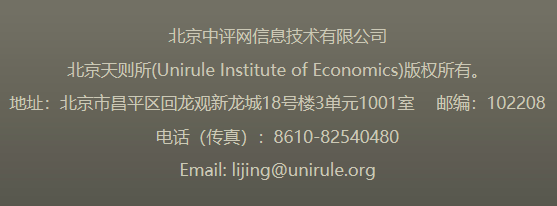不敢“代表”,不能擅自代表。
首先,感谢盛洪教授给我们写作了这样一本富有启发性的著作,感谢经济出版社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本非常重要的学术著作。这本书的名字叫《儒学的经济学解释》,横跨两个学科,涉及经济学,也涉及儒学。我下面就从两个方向做评论,一个是从当代中国儒学发展的角度讨论本书的意义,另一个是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盛洪教授这本书的意义。
首先从中国当代儒学发展的角度来讨论一下盛洪教授大作的意义。
在封三上,有出版社的一个评议意见,说的还是非常精采的。我偷懒,把这段话念一下:“盛洪教授不同于其他代表人物的政治儒学、策论儒学和文化儒学,盛洪先接触经济学后开始阅读儒学文献的。他认为经济学的内核——自然秩序哲学与儒学思想高度贴近,也从这个角度切入儒学研究,努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传统儒学思想进行转化性的阐释,突破了将儒学仅仅作为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的格局,将经济学与儒学贯通,为儒学输入新的生命基因,在儒学研究上独树一帜。”
这个评论非常精当。我们一般都会把盛洪教授当成经济学家,但是就像刚才他自己介绍的,20多年前,已深入儒学研究中,比我还早很多,并且,很快就有非常重要的思想的创发,比如关于“天下主义”的阐释,得风气之先,还有是关于家庭主义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应该说,这两个概念都是儒学思想中最重要的。现在,盛洪教授根据自己在山东大学的教学积累以及常年的思考,把围绕儒学的众多思想整合成为一个体系。我认为这,样一个体系可以是当代儒家经济学很好的起点。
从一个儒者的立场,也从经济学爱好者的立场出发,我认为,中国是需要儒家经济学的。这礼涉及对儒学之定位问题。
我们经常会把儒学和世界其他各种宗教相提并论,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儒家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在性质上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大不相同。各种宗教关心的是来世,关心的是个人生命的永恒、不朽。或许可以说,儒家也有这个维度,敬天而诚,盛洪教授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儒家整体的思考的方式跟这些宗教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儒家的视野在天人之际,而不是仅仅盯着天上,盯着神,一天到晚企求神。儒家敬天而亲民,儒家关注天人之际的整全秩序问题。儒家的学问,如同盛洪教授本书之结构,就是大人之学。大人之学是什么学?就是格物致知之学,诚意正心之学,修齐治平之学。儒家关心心,同时关心家国。
也因此,儒家在传统上一直把我们今天列入经济学范畴中的那些问题,当成其自己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来讨论,不是唯一最重要的,起码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们通常称之为儒家经典、实际应该是中国经典的第一本,《书经》,也即《尚书》中,对这个问题有大量讨论。《尚书》第二篇《舜典》记载中国第一个政府之结构。在那里,政府的第一个职能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通常会说,政府的第一个职能是提供安全,首先要阻止人与人之间相互侵害,防止外部威胁。但在《舜典》中你会看到,中国圣贤认为,政府的第一个职能是为生产活动提供良好条件,舜策命禹为司徒,负责平治水土。第二个部门,舜命周人的祖先,名叫弃,为“后稷”,其职能是播种五谷。这就是生产活动。接下来则是教化,安全是在第四位。政府还有一各职能部门,舜任命了垂为“工”,负责工业以及工程事务。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第一个政府中,负责经济活动的职能部门占了至少三分之一。这就是中国圣贤所理解的政府应有之职能。接下来一篇《大禹谟》中,禹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是中国人的观念,跟古希腊人、跟犹太人都是不一样的。
从这之后,中国就有一个非常重要、连绵不断的经济思考的传统,以及经济制度实践的传统。我们在《论语》、《左传》可以看到大量的讨论,孔子关于经济问题、财政问题有很多讨论。当然,最有名的是司马迁的《货殖列传》,这应该是第一篇经济学专题著作。还有《盐铁论》,这是一本专门讨论经济、财政政策问题的专书,由此涉及政治、观念问题。后世,儒家士大夫关于限田、均田等土地政策问题,也有大量思考和实践。
我刚才列了很多人名、书名,是是想向大家说明,在中国古典的思想和政治传统中,经济始终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儒家自一产生起就把经济问题作为自己非常重要的议题来处理。2000多年来的儒家士大夫,在其思想中,在其政治实践中,也始终把经济问题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论语•子路篇》中有一章记载孔子的治国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首先要富民,然后才有条件去教民,这是君子的两大责任。那么,怎么“富之”?一方面鼓励生产,一方面为民众的生产活动创造条件。儒家士大夫不能不思考经济学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专门列出经济学这门学科。
所以,经济学在中国是有深厚传统的,而承担主体、这个学科发展的主体就是儒家士大夫。当然,这些思考都是分散在各种各样的文献中,经学中就有大量这方面的讨论,比如《春秋公羊传》,汉代的经学家有很多讨论,后来出现各种各样的政书、比如《通典》、《文献通考》,经济学方面的内容非常之丰富。
我们今天会说,在中国,经济学方面的讨论比较分散,没有构成一个自足的体系。其实我要说,是有一个体系的,只不过,此体系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高度分化的学科体系中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就像盛洪教授这本书一样,儒家的经济学体系跟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确实不一样。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儒家的体系好,还是现在大学本科一年级所学的经济学体系好?这个问题是可以思考的。所以我要说,儒家的经济学传统,对于中国过去2000多年,或者更远一些,4000年来文明之延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这一传统在20世纪基本上丢了。现有经济学体系基本上是从国外引入的,而当代的儒学,也基本上放弃了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最早一批现代儒者,比如康有为、梁漱溟,都是非常关心经济问题的,熊十力先生晚年也颇为关心经济问题。但可惜,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儒学,所谓港台新儒学,以及受其影响的大陆主流儒学,局限于哲学或者哲学史领域,无人关注经济问题。
这样的儒学是无力回应中国和人类之需要的。应该说,儒学今日呈现出复兴的态势,而儒学要真正实现复兴,就必须面对中国人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大家都关心发财,都关心致富,国家也关心富强,而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也相当严重。儒学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唯有如此,儒学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儒学要想在今天充分的发挥作用,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学。儒学者中应当有经济学家,把原来分散在不同文献中那些思考集中起来,以现代人容易接受的表述方式将其表达出来,并予以发展。这是今天儒学不能不承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盛洪教授以其自己先天的学科优势进入这个领域,并给我们构筑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建立了一个儒家经济学的初步框架。我想,未来的学者,不管从经济学方向进入,还是从儒学方向进入,可以在这一起点上进一步深化、细化,发展出一个能够有效的回应中国的经济问题、乃至于整个人类的经济问题的儒家经济学体系。
盛洪教授的这一拓展对于儒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今天的儒学已逐渐渗透到各种学科,开始有所发展。昨天晚上在人民大学,弘道书院组织了一个活动,讨论两位国际关系学者写的一本书,《天命》,副标题是“一个新领导型国家的诞生”。刚才盛洪教授也讲到“天命”两个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突破,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现代学者尝试用中国古典观念思考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就是儒家的复活,中国古典观念的一个活化。这些学者背后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儒家的那些想法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在当代仍然是有效的,就像盛洪教授所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实在国际关系学界,已有不少人开始基于中国古典的观念、以及中国人4000年历史的实践,重新构造国际关系理论,应该说,儒学在这个学科的进展是比较快的,而在其他学科,则刚刚起步。现在,盛洪教授在经济学领域中做了一个拓展,极大地丰富了儒家理论体系,意义非常重大。这一拓展会让儒学更有效地回应现实问题,从而获得更大影响力,获得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其次,从当代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角度讨论一下盛洪教授大作的意义。
我自己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既可以如现在这样,叫做《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也可以叫做《儒家的制度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因为,这本书一方面确实是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儒家关于秩序之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发展出了一个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一努力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有指路的意义,指点方向的意义。
十几年前,我开始研究经济学,现在也比较关心经济问题以及经济学领域的最新进展,不能不说,自己对当代中国经济学之现状是不甚满意,有那么一点失望。因为,我们的经济学对于当代中国之大量经济问题、经济趋势,都不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举一个最显著的事实,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高速增长,这个增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不管明天怎么样,起码迄今为止的增长是全世界过去30多年中最好的。那么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一个经济学家给出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研究,从这个方向,从那个方面讨论一些导致高增长的因素,但我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系统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没有这样的解释,造成很大问题,首先,从理论发展的角度,中国经济学家白白流失了大好机会。本来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发展出一套理论的,这个理论有可能对西方现有理论体系有所丰富,甚至有所突破,换言之,我们可以透过对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的解释来丰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可以在理论的多个层次上有所创见的。但现在没有,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在用西方的既有理论阐释中国的事实,用中国数据验证西方理论,没有一个明显的、让人兴奋的理论突破。
若干年前,林毅夫先生说过,我们回望现代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可见,每一次经济学的大发展,都是因为某一重要国家经历了一次比较长时段的经济增长,由此而有了经济学研究中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最初在法国,后来到英国,再后来后来到美国。为什么?就是因为,最初,法国首先经历了现代增长;后来,是英国,再后来是美国。学者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在最基础层面上发展了经济学理论体系。但这一次,迄今为止,在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产生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解释体系。那么未来会有吗?我满怀期待。
更重要的问题是,若我们不能够有效解释自己的故事,我们就不能看清楚,自己在哪儿,也不清楚自己的明天在何方。我们把过去走过的路说不清楚,也就意味着,我们不知道要去哪,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中国经济今天处在彷徨、迷茫之中,速度在下降,大家都在说转型,但是,究竟要往哪去,我们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发展?大家都在说,众声喧哗,但这些意见与中国的现实之间有多高的契合合?我有所怀疑,我听到、看到过很多意见,没有说服我。因为,我有一个根本的怀疑,你根本没有说清楚我们是怎么来的,我怎么相信你给我们指出的路?你自己就没有看清来路,谈什么去路?
所以,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贫乏,不仅导致中国经济学界丧失丰富经济学体系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让处在彷徨中的中国经济找不到方向。那么,经济学何以未能有效地解释中国?恐怕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中国是什么。据我优先的观察,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解中国、解释中国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短板,不理解中国是怎么来的。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家大部分人只有能力或者意愿关心现实,关心今天发生的事情,或者最多就是30年、60年间发生的事情。知道这60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知道这30多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知道这几年经济是怎么变化的,但是,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而言,这样的时间视野是远远不够的。这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远远不能说明全部,你只看到了局部事实,仅此不足以完整地解释当下中国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
比如,大家都说,好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很重要,而刚才盛洪教授提到,制度有多种。全国人大公布的法律很重要,各地颁布的地方规章也很重要,但是,观念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影响力,很可能比法律政策还大得多,而在普通民众那里,这类根深蒂固的观念,通常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而他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我们观察一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间经济增长表现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曾发明过一个概念,“钱塘江以南中国”,涵括温州、福建、广东等地。为什么那些地方的经济增长表现最好?我的回答是,这跟那些地方的人们背后的观念有关。那些观念是什么?正是儒家的那些观念。这些观念塑造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结构支撑了经济增长。你现在如果看不到支配人们行为的那些观念,那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就是非常浮浅的。
很多人说,因为全球化开放,所以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非常快。此说缺乏解释力,对此很容易给出反证。80年代以来,几乎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开放的,大部分国家都是开放的,都卷入全球化过程中。为什么是中国表现最好?同样是中国,开放程度差不多,为什么中西部地区、东北与钱塘江以南中国相比,有那么大的差距?背后都有观念的理由。
最近,我在阿里研究院安排下,走马观花地看了几个电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现在大家都谈在互联网经济,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电商发展非常快,电商比美国还要发达。为什么?原因何在?现在有一个解释说,因为中国政府对传统领域管制比较严厉,所以人们为了逃避政府的管制,进入电商领域。这个解释基本上没有说服力。我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联系到刚才盛洪教授讲的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那些淘宝店,我估计,大多数都是以家为单位进行经济活动的。古人讲男耕女织,现在淘宝体系里的大多数网店恐怕就是新式男耕女织。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是支撑了中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我们还可以从更宏观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正好最新一期《读书》杂志第一篇文章就是讨论中国人固有的观念与互联网+中国之间的关系。那篇文章颇有意思,虽然乍看起来比较离奇,但很有意思,建议大家读一下。
上面举了这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一个是互联网经济增长,想说明一个观点:我们必须深入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为此我,们要理解中国人的观念,以及这个观念所塑造的社会结构。只有我们把这些东西理解透彻之后,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增长,以及在过去几千年的增长。这样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思考,下一步中国经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在理论上,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有哪些突破。
第三个问题,儒学能给经济学带来什么?儒学对于经济学的思考,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能够贡献什么?或者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进入儒学体系,重新思考经济学,可以得到什么?
我在前面讲到的几个经济现象,背后都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也是盛洪教授在本书揭示的,我认为也是本书的贡献所在,那就是讲到了君子,讲到了修身。这一讨论问题有助于我们反思,今天主流经济学的预设能不能成立?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在多大范围内可以成立,而在在此之外,则不能成立。
刚才盛洪教授讲到“理性经济人”,整个经济学体系奠基于理性经济人,它预设,经济人都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动的。但实际上,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发展逐渐地揭示,这一假设不能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尤其在涉及制度问题、市场秩序问题时,这个预设是非常无力的,不足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效的出发点。那么,我们怎么预设经济活动主体之偏好、心智?从什么样的人性预设出发构思经济学理论体系?
盛洪教授讲到了君子,君子是随便一个什么人,经过修身而成就得。我有时候想,可能企业家是非常接近于君子的,我更愿意把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家理解为经济过程中的君子。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君子。我们如果做这样的理解,大概更容易解释经济过程。
接下来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在这一经济舞台上活动的主体,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基于这样的状态,他们之间能够合作、交换,从而形成秩序?盛洪教授指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不足以形成良好市场秩序。确实如此。那么,可替代的预设是什么,我认为,儒家的人性论大概要更恰当一些。
儒家的人性论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中庸》说,“天命之为性”,我把这个性理解为仁。四五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不知道扔哪去了,这篇文章讨论,基于仁,有没有可能重新构思经济学的基础预设。这个想法倒也不是突发奇想,当时我在同时研读苏格兰道德哲学和儒家。大家可能都记得,斯密在他《道德情感论》一开始就讨论“同情”,所谓同情共感,这是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此处的同情,跟儒家的仁之端,非常接近。其论证有相类似的例子,斯密举的例子是,一个人拿锤子砸自己的手,旁观者会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斯密说,旁观者的反应,就仿佛锤子砸在自己手上。这跟孟子的一个说法是非常接近的,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现在拿锤子在台上砸自己的手,各位都会有怵惕恻隐之心。孟子说,看到不到一岁的孩子向井口爬去,每个人也都有侧隐之心。
上天赋予我们同情共感之情,此情之扩充,就是仁,仁让人互敬、互爱,仁让人采取合作的方式,然后就会有市场,有市场中的秩序。当然,不同的人对仁的自觉程度不同。因此,市场里会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通常会成为企业家,小人成为企业家雇佣的人,大人和小人的区别就是这里。有君子、小人之别,就有了市场中的组织,君子之主要作用就是组织企业。由此涉及企业理论。企业理论的核心应当是企业家,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企业家,组织其他人瞄准消费者的需求生产?我们经常会说,因为这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实,他追求利益的行为是包裹在一个具有同情心的情感框架之中的。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也完全可以组织一各团伙去抢劫啊,但他为什么办企业生产产品、投消费者之所好?如此追逐利益的行为,是在一个仁的心智框架中的。
这只是自己很浮浅的一点思考。但我相信,儒家可以给我们思考经济学最基础理论提供诸多启发。
再讨论儒家的另外一个观点,也许,可以对我们思考经济活动的目的,提供一个更大的框架。子贡是一位企业家,当时非常成功的商人。而孔子跟子贡的大量讨论,事实上都涉及经济学最基础的问题。特别有意思的是,孔子对仁的含义之两个最重要的阐述,都是在和子贡的对话中展开的。仁的一个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另一个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子贡问孔子、孔子回答时阐发的。由此可见,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促进了孔子对仁的思考。
孔子与子贡另外一个对话,涉及财富的目的,“富而好礼”,礼,宽泛地理解,就是文明、文化。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财富,但这个财富本身不应该是人的目的,那么,目的是什么?孔子对于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很有助益。经济活动应当置于文明繁荣的框架中,财富应当服务于文明。
自己学习过一点点经济学,近些年来对儒学比较感兴趣,一直想从事儒学与经济学的会通工作,但精力主要在儒学方面,经济学这方面一直有心而无力,所以看到盛洪教授这本书特别高兴,希望在认真拜读以后,写一篇学术性书评。上面的内容比较零散,希望能够尽快写出书评来。谢谢。
秋风:
这个朋友提的问题,应该说是文明的最根本问题,如何从家的有限的熟人范围扩展到陌生人社会。纵观人类的文明,有两个基本解决方案。中国以西各文明是通过确立一神教来解决这个问题。一神教的教义就是要解决陌生人的社会合作问题,上帝让人要兼爱、博爱。而人要博爱一切人,就必须取消小爱,所以,犹太教、耶教经文中,上帝要约伯把自己最喜欢的孩子献祭给自己,上帝也说,他到世上来就是要让家人之间相互为仇的。看起来很极端,很残酷,其目的正是要人突破家内亲情关系,接纳其他人,进入陌生人社会。这一宗教塑造了“普遍人”,由此,中国以西诸文明才有了普遍秩序。
中国人走的是一条不同的路。在中国以西,我们看到的是断裂,家与普遍秩序是不兼容的,要陌生人社会,要普遍秩序,就不能要家,就必须破坏家。各种神教都有出家、破家倾向。中国人则提供了一个保持两者兼容、连续的解决方案。《论语》第二章就是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从文本结构上看,这一章处在《论语》非常显赫的位置上,十分重要,内涵又十分丰富,又多次曲折,我们要特别仔细理解这句话。在儒家看来,我们当然有自然的亲情,并且,我们要自觉,此即“亲亲”。但仅此是不够了,我们不能停留于此。我们必须在家内亲情关系中去体会对待家外陌生人的普遍之道。“本”就是根,从根生长出大树,人是必须面对陌生人的,跟你本来没有关系,但碰见他,你仍然有敬、爱之情。这就是仁。仁是人之成为普遍人的依据,我们在家内孝悌体认之,但要从孝悌扩充,才有仁。理解了孝悌和仁的关系,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圣贤是如何解决人之精神突破问题的,如何解决普遍的社会秩序之可能性问题的。简而言之,依照儒家之说,我们在家内习得敬、爱陌生人之道。因此,爱有等差,但无边界。由此,中国也就有了普遍秩序,比如,天下。
应该说,这两者都让普遍秩序成为可能。但在我看来,中国圣贤、儒家的解决之道,更为自然、更为健全。西方一神教的解决方案,看起来效率极高,但实际上诸一神教之间的冲突,就让真正的普遍秩序完全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上帝死了,怎么办?博爱是基于上帝的命令,如果上帝死了之后,人如何具有博爱之心智?儒家的办法更自然,因而更普遍,也更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