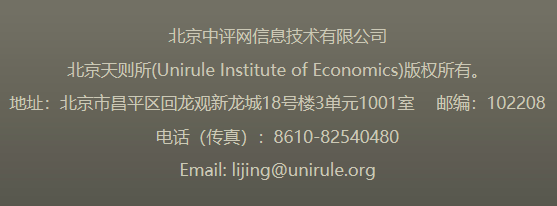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刘业进
今天感谢天则所,有这个机会参加新年期许,跟这么多老师能够见面。
我简单做了一个PPT《政府的两种职能与准入自由改革》,主要观点来自哈耶克的《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两本著作。然后把这个理论洞见与中国改革现实相结合,提出一点期许。
首先我说说政府在合作秩序中的位置,我们怎么去看政府这个角色。
第一种:认为政府纯粹就是再分配,一点都不创造财富,他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个人和企业创造的财富,所以每一分钱都是寄生性质的,直白的说,政府征收的每一笔税费都是抢劫,这是自由至上主义的看法,这是不对的。
第二种:把政府看成是正义的化身,政府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人民着想,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我们都要服从,这也是不对的。有时候人民自己不会安排长远利益的事情,而更加倾向于短期利益,因此政府举办很多公共工程其实也是有利于人民的,虽然短期中人们不同意。
我想一个政府其角色的恰当定位应当是——政府是分工合作网络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点。就像每个企业处在分工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一样的,政府也是,只不过它是一个特殊“供应商”,概括的说,政府供应“法律和秩序”及其他公共物品。这不是政府跟市场两极的看法,而是在分工合作的网络之中,每一个节点都少不了,不要把政府特殊化,也不要认为无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作为一个分工节点,政府提供两种东西,一种叫法律与秩序,另外一种叫其他公共物品,它是两种东西的供应商,相应地,享有的是两种职能。一种叫统治性职能,基于这种职能,它提供法律与秩序,履行这一职能需要以暴力为后盾;另一种提供服务性的公共产品,履行这一职能不需要也不应当以暴力为后盾。我们纳税人给它用税收来购买的,就是这两种东西。分工节点的视角来看,这里就存在一对交换关系,它给我们提供上述两种东西,我们纳税人给它支付税款。买方是纳税人,卖方是政府,虽然这一买卖关系比较特殊,但基本的买卖合约和买卖性质是确实的。布坎南开创的公共选择学说,主要就是阐明了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这一对交换关系。
不过问题没这么简单。政府提供“法律与秩序”也就是洛克讲的“广义产权”时,法律秩序无非就是保护我们个人、企业家庭的这些生命财产与自由,就像市场中的镖局一样,一个保镖或私人保安公司一样,保护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还要仲裁冲突,保护国防等等。用哈耶克的说法,统治性职能就是履行文明社会中的“正当行为规则”,保卫国防和强制征税。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政府是需要权威的,甚至需要某种特权和尊严,而且现实这还需要适度的、必要的奢华。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觉得政府越简易越好,花钱最少越好,但事实没有这么简单,政府需要适度的奢华,我后面会讲这个道理,埃德蒙.伯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提供法律和秩序的时候采取的提供方式是垄断。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存在几套竞争的法院系统和国防军。
再看第二个职能,就是所谓的“服务性职能”,我们把它叫“其他公共物品”,最常见的就是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养老保险和住房保障等等,也包括防疫疾病、天气预报、救灾、数据统计等等。在生产和提供这些物品的时候,它的地位和资格立马就改变了,这时,政府跟市场中其他的社会组织和私人企业完全是同等地位,这点在转型国家甚至在西方国家里都有意识地被误导了、忽视了。政府履行做服务性职能的时候没有任何特权,根本不能垄断、而只是社会中的平等竞争主体。比如义务教育通常认为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有责任与只能由政府来做某件事是性质上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政府有责任举办义务教育绝不是说只有政府才能做义务教育这件事,想想我们国家的现实,不说义务教育完全政府垄断,就是企业办个幼儿园拿到许可证比登天还难。理论上,道德合法性上,任何私人企业、任何宗教教会,总之任何合法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做义务教育这件事情。这一点人们长期以来被政府误导了,以为举办某一事业是政府的责任,等同于唯有政府才能做那件事,别人不能染指。在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外的其他任何非统治性职能的服务性职能时,政府不能够用那种第一种职能的权威适度的奢华那种权威独断的地位,尤其不能以暴力为后盾来提供服务性职能。
统治性职能与服务性职能之区分,不仅仅是简单的两分法。服务性职能的唯一提供方式是平等竞争,你政府在履行这个职能时跟其他市场上和社会领域中其他组织是平等竞争主体,没有区别。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政府在履行服务性职能的时候,它总是盗用履行第一种职能的权威和特权,复制其提供方法。第一种职能中例如法院和警察系统是需要暴力,监狱也需要暴力,征税有些情形下也需要暴力,但办义务教育、办医院、办加油站、炼油,开办航空公司这些东西不需哪怕一丁点儿合法暴力。很不幸,现实中,我们事实上看到政府借助了第一种资格做第二种职能的事情,即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威的、垄断的,甚至拥有特权和适度奢华的那种资格,来去做第二种普通的事情,履行服务性职能。这在今天的中国太普遍了。在政府提供服务性产品的每一个领域,它本来跟市场主体没有任何区别,但它却盗用了第一种职能的资格、形象,也盗用那种权力基础,以暴力为后盾,以垄断方式提供。长期如此,以至于人们认为政府垄断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医院、航空运输、养老保险……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大错特错。
关键不是简单的两分法,为什么?你盗用统治性职能以暴力为后盾的资格时,那种独断的资格其实是不道德的,你没有资格盗用。比如贺卫方老师很有名,我盗用他的名义来为自己牟利,是不道德的也是非法的。
在履行服务性职能场合居然用垄断的方式,还泰然处之,这极不正常。义务教育是很普通的东西,医疗服务也是很普通的东西,为什么只有政府才能做别人不能染指?你们看到哪一个私人企业能够做义务教育吗?好像在今天都成了一个常识了,这是政府做的事情,你们不能做。现在我要重申,告知所有人,政府所的服务性职能的任何一种产品,都必须是平等竞争地提供;政府有责任做,做就是,但是不能阻止任何其他组织如私人企业、社会组织、非赢利组织等任何人,包括国外组织都可以来做(如果效率高质量好)。但是我们现在常识不再,因为长期地、独断地做这种服务型职能,我们就以为只有它能做了,就用垄断的方式来提供,所以我们要重新翻转这个伪常识。
除了道德直观上的好坏以外,还有更深的、不容易觉察的一方面,即政府以垄断方式去做服务性职能,它其实阻止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核心作用:发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一个发现程序。如果人为垄断以后,来自市场竞争的发现程序不能运转了,这就会导致服务性职能的那些所有产品/服务的真实价格无法发现,合适数量无法发现,令人满意的质量无法发现,新技术跟进迟缓。教育多少花钱、医院到底要办多少个、学校和医院如何空间布局,医药价格到底是多少,无法发现,它垄断断了,它说多少就多少。
上大学一个学生学费5000,也许是8000,不管高还是低,垄断了教育,真实价格就无法发现。在经济学上,价格不是一个会计核算的问题(垄断举办的主体倾向于虚高申报成本)。经济学有个基本道理,真实的价格唯有一个方式可以发现——那就是竞争。比如手机多少钱,原来1万,现在8000、5000、2000,300块钱都可以买到一款质量过去的去的智能手机。这个价格是怎么来的?谁定的?就是许多家手机厂商竞争出来的。如果你当初只让一个手机厂商生产,现在还是1万块钱一个。此外,在中国,汽油价格是个典型例子,原油的国际油价大跌,我们这儿汽油价格反而大涨。所以政府垄断服务性职能,所有相关的产品如教育、医疗、社保、医院所有的东西,包括航空、石油、电信资费,无一例外。这些产品的真实价格无法发现,均衡数量无法决定。一个地区,幼儿园、小学到底办多少个适合,无法确定数量,空间布局靠拍脑袋决定,唯一的原因——竞争机制被人为阻断了。
只要垄断,“其他公共物品”的价格、数量、质量这三样都无法发现。只要人为阻断这个作为发现成都的竞争机制,相关产品的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就被阻断了,所以,改革的办法,最关键的就是——准入自由。准入自由的制度条件能够确保什么东西应该进入到政府提供的服务型范围;以及确保相关产品的资源配置优化(价格/成本、数量、质量)。因为刚才我说了要竞争性提供,例如教育,政府提不提供,如果需要政府出马提供需要提供多少((0,1)选择)?如果你在开放的情况下,说不定有的根本不需要你提供,所以还发现一个选择,这事我该不该做、我如果做的话做多少。该不该做(0-1选择)为什么也能发现呢?因为你是开放的,结果如果民营企业做的比你更好,人家都不要政府提供的,就表示你不需要做。医院需不需要办、大学是否需要政府办那么多,或者有的事根本就不需要你做,因为你是开放的,就意味着别人跟你竞争,竞争的结果自动决定你的具体职责。
发现该不该做,是很重要的发现;该做多少,也是很重要的发现,二者都要准入自由这一条基础规则来保障。如果发现你该做,那么你做多少的问题也是一个发现,你做多少、以及做什么质量、做多好数量、学校和医院还涉及空间布局,也是要靠竞争来发现。准入自由是最核心的、一个纲领性的制度条件、保证。在准入自由条件下,如果民间企业和私人市场能够充分地提供,那么政府就要退出,就不应该列入政府服务的菜单,所谓的民生工程就跟你没关系。
发现广义公共产品的价格、数量和质量,我们就找到一个简单的对应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法律和秩序、基础设施,义务教育这些所谓的民生,个人和企业给它交税。但是这个税收来支付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值不值,是买贵了?有些东西是不是该购买?这些都是发现程序来保障的。
法律和秩序这种垄断的东西本质上也是要发现的,只不过,这个竞争程序是另一医类金竞争——政治竞争。通过政治传统、民主选举竞争、国际比较和公共选择,来保障法律和秩序的数量、质量和价格。我们的宏观税负水平应当是多少,与它提供一揽子公共产品是物有所值吗?现在中国的真实宏观税收水平在50%以上,我们“购买”到产品值那么多吗?归根到底,法律和秩序;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等等,这些要靠民主选举、市场竞争、公共选择,核心机制就是竞争性的机会(竞争性政治机会和竞争性经济机会),即准入自由。
我写了一篇文章《明确中国的福利政策该怎么搞?》,结论是,自愿福利制度加辅助性的和临时性的政府社会保障,政府有责任做某些事情,但必须开放准入,开放市场。
无论是法律秩序还是民生领域也好,最核心的特征(制度条件)就是准入自由。
我们看看身边的事情,企业可以办一个幼儿园、加油站、电信服务商吗?都不可以,这就是准入不自由。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进一步思考,难道我们公民跟国家仅仅是一个交换关系吗?我给你交税了你给我公共物品,仅仅是一个买卖关系吗?也不是。我看到伯克的东西以后就没有简单地说,我们只是买卖关系,我跟你讨价还价,你必须货真价实,道理是这么讲,但我们跟国家之间不是仅仅的买卖关系。所以为什么在提供法律和秩序的时候,政府要适度地奢华、要有威严,要带着一丝神秘的面纱,这里有很复杂的道理,这是基于不完美人性的前提下制度进化决定的。对此我引用伯克的一段话:
“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但国家却不可以为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为了一些诸如胡椒或咖啡、布匹或烟草的生意,或某些其他无关重要的暂时利益而缔结的合伙关系,可以由缔结者的心血来潮而加以解除的”。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么做不好,它提供的产品不好,就如我们找一个物业公司一样的,我们业主也会重新找一个物业公司。何种形势下?当政府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重归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诉诸自己的自然权利。不是我们重新选政府,不能随便这么来。伯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如果暴政发展到了极点,政府的暴虐令人忍无可忍,那么,人们就诉诸自然权利,将其推翻。”(伯克,2012《自由与传统》,6页)
到了那种至高无上的必要性,不容思考、不容讨论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回到诉诸自然权利,我想到的例子只有伊朗和北朝鲜可以诉诸自然权利。在中国,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端暴政了,我觉得还是没有,但“准入自由“改革迫在眉睫。
谢谢!
[ 刘业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8-1-9在2018「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