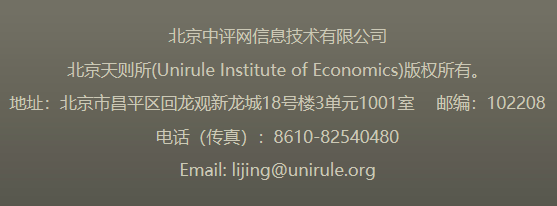感谢天则所给我这个机会和平台。本来今天赴会是为了一睹张先生、盛老师、秋风老师等几位神交的老师的风采的——几位的文章我读过一些,今天能忝列其中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没想到还能在一起谈经论道,令我喜出望外,同时也有点紧张了。我从事日本近代思想史及其相关领域有20年了,听了刚才几位的发言,很受启发,有很多感想,有些我很赞同,有些也有保留意见。我没有准备稿子,所幸这些内容都是我长期学习和思考过的,比较熟悉。我看了一下今天发给我的这份参考资料,差不多都是有关儒学的。因为有这个标题,还有刚才几位发言对我的启发——这些都是我的提词器,所以可能谈得比较漫谈一点,但估计不会跑题,努力做到形散神不散。
首先谈谈东亚。东亚的一体化到底存在不存在?我觉得从历史角度讲是有的,近代以后的东亚意识就日趋薄弱了,特别是现在,确实缺乏一体感。东亚指的是什么地方?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首先要厘定,否则不大好谈问题。看这个材料,内容都是有关中日韩的,应该是东北亚,历史上固然儒学把这个区域贯穿起来,联系起来,但除此之外还有大乘佛教,它的作用也很重要,无法忽视。从儒学和大乘佛教这两个维度来看,越南在文化上也可以概括进去——盛行儒家文化,其佛教也是大乘系统的,同其它中南半岛各国信仰小乘佛教迥然而异,虽然在地理上属于东南亚,但是文化上应该是东北亚的。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一般把东北亚和东南亚一起称作东亚。这样,东亚区域中就包括了东南亚穆斯林各国,存在着一个伊斯兰教世界。我感觉我们今天议题中的东亚是一个“文化东亚”,以中日韩为主,历时地看,还应加上琉球和越南,姑且称之为“文化东亚”吧。现在,好像涉及文化东亚的学术会议大都没有越南学者参加,是越南学者缺少文化东亚的自觉意识呢?还是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会议主办方没意识到从而没有邀请呢?总之越南似乎被文化东亚给遗忘了。
秋风:
现在慢慢有了。
马铭:
这样,概念厘定了,问题也好谈。另外还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基于以上认识,我现在谈的也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届时我会及时禀报出来,以免造成时空错乱。我感觉到儒家从历史上来看,确实在东北亚是大家很认同的一种文化、一种价值,都很追求它,尤其是韩国,但这也有个时间段的问题,不是说韩国和日本在历史上一直就是儒家文化的一统天下。还有,一提到中国文化影响就一定是儒家的影响,这个可能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在东亚,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与汉字文化圈重合的佛教文化圈。日本是17世纪初,进入江户时期后才把他作为官学,此前主要是信奉佛教,不但有来自中国的各宗派,还有自己的独特宗派,比如“日莲宗”了,“时宗”了,还有“净土真宗”,也叫“一向宗”,它实行“肉食妻带”,就是可以吃肉和娶妻,可以生子继承寺院,这一点恐怕在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前的世界各文明区域的宗教中还没见过。奈良时期(710~784)的佛教为镇护国家而祈祷,是皇室和贵族的宗教,以致尾大不掉,终于为躲避佛教势力而迁都。平安时期(794~1192),原附属于政治的奈良式都市佛教转变为山林佛教,既拥有拒绝国家权力的“圣域”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主张“王法和佛法如车之两轮”,标榜自己为“护国佛教”。10世纪后出现僧兵、教团,形成宗教门阀,皇权旁落,不少天皇急于传位而喜遁佛门,成为法皇。佛教势力本身就是封建主,各宗控制着广土众民,拥有庞大的教团武装。镰仓时期(1192~1333)的佛教各宗在进入室町时期(1336~1573)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教团。在16世纪,净土真宗教团与世俗诸侯争斗不已。相比之下,中国的汉传佛教基本处在国家的掌控之下,也因此给予我们佛教是和平的宗教印象。从文化和历史的视点来看,汉传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缺乏世俗的势力,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佛理的探讨和佛法的普及以及其手段上了,并且那些弘扬佛法的方式方法中有不少转化成了文学艺术的形式,比如,弹词、鼓词和话本,而话本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章回小说了。在韩国,程朱理学成为官学要早一点,大概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此前的高丽是儒表佛里的。高丽的崔氏政权曾为祈祷退散蒙古军队而耗时15年复刻此前毁于蒙古入侵的《高丽大藏经》,这反映出佛教信仰的习惯和力量。高丽时期韩国佛教势力是很大的,以至李朝必须进行废佛扬儒来为程朱理学成为官学扫除障碍。
在程朱理学成为官学之前,儒学对日本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对韩国的影响也没有我们现在常说的那么大。其实,在日韩两国,儒家文化在成为官学以前较多地集中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外交领域,而较少地体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统治全社会意识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佛教和本土信仰。从文化和历史的视点来看,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缺乏世俗的实力,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人们心灵的救赎和佛法的普及以及其手段上了,并且那些弘扬佛法的方式方法中有不少转化成了文学艺术的形式。现在日本人和韩国人以及我们汉人——我们有56个民族,这里我主要说汉人——尽管外貌上很难加以区分,文化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汉人还是与他门不同之处也很多——至少佛教在文化中占的比重是不同的,对人的心理气质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有所不同,西方人区分不出来,我们却可以辨别出来。比如,历史上,除了个别天皇有所例外——可能是仿效儒家厚葬文化的结果——日本人不分贵贱基本上都实行火葬,没有任何心理抵触;韩国人尽管相当儒家化,但不像汉人那样强调气节。再比如,我们独有的玉文化与汉族同步发展,与。我们常说“上下五千年”,其实应该是“上下八千年”,玉的历史就是八千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就是安排展品的。汉语中同玉有关的字和人名、表达非常多。在于文化上汉人与日韩截然不同,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特质。
佛教在日本历史上起的作用非常大,我觉得这一点国内学界重视得不够。历史上,日本佛教势力本身就是封建主,各宗控制着广土众民,拥有庞大的教团武装。京都是室町幕府(1336~1573)所在地,从8世纪末到近代迁都东京一直是日本的首都,寺院在全日本是最多的,其中很多都毁于佛教教团间的战争及其同世俗封建主间的战争,规模、惨烈程度和社会破坏性不亚于历史上的欧洲。就是到了江户时期(1603~1868),佛教各宗的经济实力,称为但是日本近代编写史书的时候,这一段可能是有意的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可能就是近代民族国家的问题了,近代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建构时总是会对过往进行重新审视和取舍,往往会留下那些闪光的东西而舍去那些暗淡甚至丑陋的因素,总之要撇出那些不利于建构民族国家的因素。我们看日本现在民族主义很强,日本人说中国人民族主义很强,各说各话,说的都有正确的一面,也有不准确的一面。我们要分时代,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近代以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很强,尤其在二战之前的那段时期。日本民族主义和我们不一样,18世纪起步,19世纪80、90年代才成型,20世纪初进入高潮。我们近代以前民族主义的因素比较多,尤其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因素,有特别是在上层,但民众基础差强人意。近代以后,因为近代化的建构我们落后了,所以民族主义的发展比较停滞,甚至需要外部力量的倒逼,也就是说中国民族主义是在救亡图存的大环境下进入高潮的。大众的参与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后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民族主义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我们说中国人,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不是汉人?我们说这个概念100多年前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孙中山和同盟会最初借用了朱元璋曾用来号召汉人反对蒙古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实际上就是汉族民族主义,后来发现不妥,就进行修正,号召五族共和,但我们今天所说的其他少数民族没有反映进去——国民政府把他们都看成了汉族系统下的部族,1949年后经过30年的民族认证工作,才有了今天中华大家庭中的56个民族,这在认识上这显然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秋风老师刚才谈到了民族国家及其存废问题的问题,对此我有点不同的认识。现在世界近代史可能就是一部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现在欧洲又一次出现民族问题了,法国大革命以来这已经是第好几次了,看来欧洲的民族主义也还没有收官,可能又将迎来一轮新高潮。
下面我以日本为例展开谈一下民族主义的问题。日本的民族主义虽然可以追溯到18世纪,“国学”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是针对外来的佛教、儒学以及以荷兰文为媒介的西洋学“兰学”而言的,日本文化人在文化危机中做出的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民族主义性的反动,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但真正的民族主义是需要大众高度参与的。民族主义的核心因素是认同,起初是种族认同的成分多,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交往日益密切,彼此和对世界的认知逐渐扩大和深化,文化上的认同很快逐渐占了上风。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日益发达的交通、通讯和出版・教育・文化事业等文明的进步大大强化了一定区域的人们文化上的认同,强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我们今天所说的日本民族主义的真正形成是在19世纪80、90年代,与近代日本的近代国家建构是同步进行的。19世纪中期的两本书——一本是亨利・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1857~1861),实际上是英格兰文明史,还有一个就是弗朗索瓦・基佐的《欧洲文明史》(1828)——在明治时期的前十年被引进日本,出现了一个文明史热,明治日本全面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流行的文明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从“野蛮”经“半开化”到“文明”,分阶段呈直线演进的,有了一个明确的关于文明的自他定位。福泽渝吉就接受了这种史观,把中日韩都定位在半开化之列,并在1875年出版了该贯穿该史观的《文明论概略》,其中第二章就是“以西洋文明为目的”。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刊物集中出现在1880年代,如《国民之友》、《日本》、《日本人》等,“国粹主义”运动高涨,其近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过了10年,福泽渝吉就在《脱亚论》(1885年)这篇社论中认为日本是文明国度了,而中韩还停留在半开化之列,他的这种看法通过刊载该文的《时事新报》得到放大并广泛传播。反观洋务运动那三十来年,成绩的确不小,但是毕竟遭遇了重大挫折,所以自然有些教训,我感觉到至少有两点,尤其是对比明治维新时就比较明显了——其一是法治的缺失;其二是对新闻出版事业的不重视和由此造成的不发达。同光年间的中兴名臣那么多,但都好像在建构法治国家上罕见有什么建树,人治政治依然故我,第二点与第一点密切相关,人治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而权力本身不愿意透明,不愿意接受监督,不愿意与民众协商而达成共识,而没有共识就影响共同的认同,难以形成广泛的参与,于是就难以铸就成熟的近代民族主义。我们现在是不是走出近现代=Modern Times了?可能还没有。既然如此,就是处在民族主义建构的过程,完善的过程,深化的过程。近现代是一个结构,后现代是重新审视和检讨作为民族国家的国民在近现代的所思、所为、所感——也就是民族主义——的过程,是一个解构和重新结构的过程。中国还处在近现代阶段,不像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了,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时点来说,民族主义的克服和超越是一个一般将来时的问题,而不是现在进行时的问题,这对于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的中国来说未免有点奢侈了,但是我们可以探讨,因为我们是做学问的,是追求价值的。
所以今天题目很有意思,除了东亚,价值也是一个关键词,还有“标准”。不过主语省略了,主体是谁?这个主体很重要,并且还关系到“标准”,所以下面我想谈谈主体性(Selfhood/Self-direction)的问题。陈奉林老师刚才提到日本和韩国在吸收中国文化时有一定的主体性。对此,我们估计的还是太高了,比如日本选择性吸收中国文化,我觉得那是因为日本近代以后发达了,我们看待它的历史时往往容易高估,实际上历史主义地来看,当时并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来消受需要巨大物质实力和文化实力支撑的一些中国文明要素,比如科举制度,日本曾在8世纪初首次举行进士考试,但为时不长,后来就停办了,原因就在于不当时的日本软硬条件无法支撑,也就是说不符合当时的日本国情。再比如女性缠足,以丧失女性劳动力为代价,这需要一个社会具有相当的生产力才能消受得起,即便是在近代前的中国社会,它也是汉族上流社会的一种奢侈,根本没有普及到需要女性劳动力的下层民众之中,古代日本、韩国和越南就更是消受不起了。科举和缠足之所以没有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并不是由于历史上日本统治阶级有多么高明——不是在进行价值判断之后加以摈弃,而是无力为之。
现在似乎说到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国学就是儒学,国学院就是儒学院。其实,宋代就开始儒道佛三教合一了,至今已有一千年了。“国学”这种说法好象来自于日语——何时借用的我没有考证,通俗地讲就是日本民族固有之学,形成于18世纪,是研究日本古代语言、文学和制度・习俗等文化的学派,其重点是通过上述研究来厘清受到儒佛文化影响前的古代日本文化固有的特性,其本身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物。有鉴于此,我们所说的国学通俗地讲就应该是中国民族主义之学,所以国学院至少应该包括儒道佛三学,其实还应该包括中国化了的伊斯兰之学——回教之学——我姑且如此称之。就拿作为国学的儒学来讲,我们的认知可能缺少一些应有的主体性。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点。被拖入近代后,我们先是抱着传统文化曾经高高在上的地位不放,舍不得,不愿意使它与时俱进——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确实可以理解,你放到任何一个国家它都不舍得。但是,外界的逼迫可不管你那一套,我们实力不如人了,并且这不是打嘴仗的问题,现实当中固守不住了,于是就有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甲午战后,认识到日本因能与时俱进而软硬实力大增从而打败我们,倒逼着我们穷则思变,终于想改弦易辙了,于是有了小众式的戊戌变法,但因没有形成全民的共识而很快失败,导致列强瓜分狂潮,继之以庚子事变,至此我们彻底没有信心了,好象中国文化没有价值了,于是西学就没有阻碍地在中国大行其道。所以我觉得是从1901年开始,很多国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在这种大背景下,传统文化自然就命运多舛了,儒学也自然难逃其衰败的命运。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儒学之衰是良莠不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当然有其顽强的卫道士,加之其固有的道统的发挥而得以保存下来。很显然,上述过程是一个无奈的主体性逐渐丧失的过程。
其实,儒学本身是不断进步的,由孔孟的经典儒学,经汉学到宋学,再到阳明学,近代后诞生了谭嗣同的《仁学》,继之以20世纪的新新儒家(相对于“新儒家”的宋学)而言,再继之以二战后的三新儒家(私造语,恕我姑且言之),现在又有了我们大陆的新生代儒家,可见中国儒家的精神是“与时俱进”这四个字。《仁学》是经过近代化了的儒学著作,我们对此似乎重视不够,在大陆还不如海外受到重视,也因此似乎研究的也不多。日本的儒学是近现代化了的,其佛教也经过明治四五十年的近现代化,吸收了不少基督教新教的形式和内容,例如可以结婚生子。也许从这个角度上看,许多国人说日本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换个角度说,不是日本没有真正的佛教,而是我们大部分的佛教宗派没有完成近现代化。还有,我们总是围绕中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争论不休,甚至有国人说中医是巫医,传统主义者就接受不。我觉得其中存在误解。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从历时的视点来看,应该包括传统的和近现代这两部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医”,英文是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这只是其中的中国传统医学——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与时俱进的近现代化改造,但主要还是传统的部分居多,韩国的东医跟这个差不多,以药学为主,主要内容是自然医学。中医的英文应该是Chinese Medicine,应该还有一个MCM(Modern Chinese Medicine,近现代中国医学),而我们所说的“西医”的英文是Modern Medicine——至少北京的各三甲医院是这么写的——并没有表示西洋的“West/ern”或“Occident/al”,显然是被省略了,这恐怕是西方人表述时的立场,还意味着事实上存在着一个Traditional Western/Occidental Medicine。那么这种说法是先有中文呢?还是先有西文?我没有进行过概念史的考察,不太清楚,但反映出来的却是有一个主体性缺失的问题。西方人说自己当然不用说西方的了,他说我们时需要加上一个“中国的”。中医的概念如此混淆和错位,很多概念认识不是很一致,使我们产生一些无谓的争论,所以效果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说到底还是近现代性(Modernity)的差强人意,还有主体性发挥的不够充分。反映出的还有传统中医近现代化的差强人意。如果传统中医近现代化的发展到位了,中西医在文化上就平等了。
再回到上世纪初。1905年废科举,西学大行其道,近现代我国的很多名士都是那个时候接受的初等中等教育,以西学为主。再过一段,一战爆发、结束,今年是爆发一百周年,使人浮想联翩。关于一战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似乎认识得还不够充分。这个时候中国传统才开始被西方认识进而被国人认识。何以如此呢?原来,通过这次大战,斯宾格勒等西方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化没落了,这样下去的话西方就完了,于是将目光转向东方,重新认识和评估中国和印度的文化,而此前。中国和印度,特别是印度,在西方人眼中是停滞落后的,需要西方文明的救赎。于是,从一战以后中国传统文化马上就有了价值,并且可以拯救西方。正好我们1905年后新学教育出来这些人在欧美留学,特别是在欧洲留学,确实感觉到鼓舞,也终于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当中不少人内心都纠结甚至撕裂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学习最用功的时候,这时候学贯中西的这些人回国后便致力于融合传统和先进现代化。而同时代的大部分人却一如既往地继续和深化反传统,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又开始被五四反思,有一个中国文化论战,是一战以后开始的二十年代,包括三十年代,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近代不是说谁高明,都是历史中的人,他对历史的反动,一种是理想,现实中是很难的,很容易随波逐流,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嘛,
往往就容易识了大体。但是主体性的发挥要是不充分或者缺失的话,你看问题就会产生偏差甚至出现缪误。
我看了看发的这些材料,所以最后多少得谈点粗浅的看法。首先,我觉得中日韩之间的联系,在意识形态、文化方面不只是儒学,还有汉字和佛教——这一点我谈的比较多了,恕不赘言。还有一点,我觉得把这个儒家或儒学——我在这方面学习不够,可能搞错,欢迎大家批评——当成我们中华民族的大救星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是也不能把它作为中国近代落后的替罪羊,儒学就是儒学,它首先是一个自为的价值系统和情感系统,按照新康德主义的说法,它就是一种文化。我举一个例子,犹太教之于以色列人,大家一定不会感到生疏,可是不是认真考虑过有关他们的事情?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和逻辑,犹太教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以色列人怎么了?!以色列的现代化跟犹太教的传统是非常矛盾的。但是以色列人求之于犹太教的是什么呢?我思考了几年,觉得他们要求的并不多,似乎主要是身份认同——我是犹太人,希望籍此首先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除此之外,似乎没有过多的要求——这可能由于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二位一体——不像我们,一会儿孔子是社会、民族和国家进步的罪人,一会儿孔子又成了无所不能的大救星,好像我们总在这个历史怪圈中循环而无法走出去。按照一些国人的逻辑去看,犹太教乃是亡国灭种的宗教啊,怎么以色列人居然会不离不弃,甚至爱之有加?!是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有问题吗?我国各个阶层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评价都很一致而且很高,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对于他们的宗教我们是否认真评估过?它也分左中右,也有正统派、保守派和革新派,而且三派势力均衡,和而不同,是否值得我们借鉴一下?我们对儒学,我们不能苛求他,好像毁也儒学,兴也儒学似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历史的和客观公正的态度。以色列之于犹太教的这种态度和关系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他山之石?文化的与时俱进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是一个大课题,至少有三个部分需要认真对待——是否应该做?是否有能力做?如何去做?日本人做到了,犹太人做到了,相信我们也能够做得到。谢谢大家!
[ 马铭 外交学院日本研究中心讲师。 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新浪博客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9-15
中评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