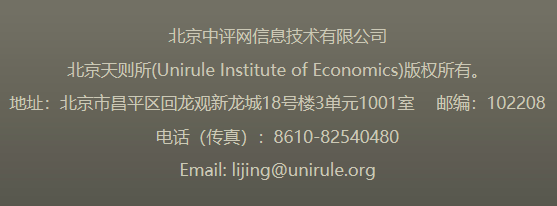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的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想从学理上探讨一下这次会议的几个关键词,第二部分谈一下我国对外交往价值观的设计问题。
文化与价值观
有人说,北大的学者,分为几派:启蒙派、学院派,“精致的现实主义”,我大约算是学院派。因为,我思考问题,总是较多地看学理上有什么支撑。像“文化异同”、“价值标准”这样的概念,从学科的定位来看,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做出的成绩最大,所以要理解这些概念,得有对文化人类学这个学科的了解。其中,关系最接近的一个学科,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叫“心理人类学”,它的前身是“文化与人格”学派。大家知道“国民性”这个词,它是指一个群体由文化塑造的性格。二战前后,国民性研究特别盛行,搞这个研究的,多属于“文化与人格”学派。说到“国民性”,大家会想到鲁迅先生怎么说的,林语堂、台湾的柏杨怎么说的,其实,这些都是文学色彩的国民性讨论,不是学理性研究,学理上的研究,就是“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它属于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二战以后,国民性研究衰落了,但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Francis L.K.Hsu,1909-1999)继承了这个学派,他开发了一些工具来理解文化异同和族群的性格。许烺光把自己的学说定位为“心理人类学”,但我觉得“心理人类学”无法涵盖他的学说。这些年,我把他的理论作以梳理、补充和发展,在其学说基础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称作“心理文化学”。
我们知道,文化有很多定义。心理文化学把文化理解为“人行为背后的原理”,一种类似生物基因的东西。现在的中国人,之所以还可以理解孔子时代的那些经典和那个时代人的行为方式,说明我们跟两千年前的中国人还有某种一致性,我们身上有一种类似生物基因的东西在“遗传”,我们就叫这种东西为“文化”。心理文化学把“价值标准”、“价值观”定义成某个族群的某种心理取向,即人们认为什么是有价值的,哪些是好的,这种取向称为“心理文化取向”。心理文化取向常常指向某种目标,称为文化目标。我们观察一个文化群体,都可以看出有某种取向,这种取向都最终指向某个目标。文化不同,人们的心理文化取向和文化目标也不同。中国人的心理文化取向是什么?是“人伦中心”,即中国人把生活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上了,认为这是最有价值、最值得追求的。这种取向指向哪里?指向“人与人之间的彻底和谐”。西方人的心理文化取向是“个人中心”,这种取向的目标是“个人的彻底自由”。印度教徒的心理文化取向是“超自然中心”,目标是“人与超自然的彻底合一”。日本人的心理文化取向是“对人关系中心”,目标也是“人和人之间和谐”,但它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对一个更高权威(过去是天皇,现在可能是公司的头头,或某一权威存在)忠诚条件下达到和谐,为了这个忠诚,有时候可以牺牲和谐。在心理文化取向和文化总目标相互作用下,人的行为会发生整合,逐渐形成一个“价值观束”。中国社会整合出的“价值观束”,包括忠、孝、仁、义、礼,三纲五常等。西方社会整合出的“价值观束”包括“独立”、“自由”、“人权”、“民主”等。印度教社会整合出的“价值观束”包括“梵”(宇宙灵魂)、“阿特曼”(个体灵魂)、“法”(“达磨”)、“解脱”等。“价值观束”是长期整合出来的,不是人为拼凑的;是自洽的,不是矛盾的。只要人人都按这些价值观做了,就能实现该社会的文化目标。当然,你可以说,“心理文化取向”和“文化目标”只是一种假设,但这个假设不是凭空说的,是根据文献和人们的行为概括出来的,还可以从人们的现实生活来进行验证。
最近一些年,国民性研究又有复兴的动向,起因是人们的文化认同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世界在变“平”,人们开始出现这样的困惑:“我们是谁?”“我们会变成美国人吗?”“我们的文化特性到底在哪里?”这就是寻找文化认同(identity),寻找那种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的独特性。这种特性,类似某种“国民性”的东西,所以,今日研究文化认同,也可以称为一种新的国民性研究。旧的国民性研究受到批判,并不是说,对一个族群特性的探究没有必要了,心理文化学可以说是一种国民性研究的升级版本。
学理上讨论了“文化”与“价值”问题后,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了。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24个字,三个层面,几乎把所有的好词都用上了,但是,把能够想到的好词放在一起,就成了人们的价值观吗?不是。前面说过,价值观是文化长期整合的东西,它体现在我们的传统中,融合在人们的行为上。这个东西,人可以去提炼和概括,却不能创造。创造出来的,只能说是一种希望,一种理想。譬如,现实中,有的人嘴巴长得好看,有的人眼睛好看,有的人则是鼻子好看,你想把每个人好看的部分,都集中到一个人的脸上,这是一种理想,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人。即便能集中到一个人的脸上,也不一定好看。设计价值观的人,大约没有文化人类学的背景,特别是没有心理文化学的背景,不知道价值观与文化是怎么回事,所以,设计出来的价值观,就像是去花店买了一束花,插在花瓶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但只有审美价值,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现在设计出来的价值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标准太高,难以达到。比如说,个人层面的“友善、诚信、敬业、爱国”四个词,把“爱国”作为个人层面的价值观,就太高迈了。人要做到爱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知道国家是什么,政府是什么,知道了“爱国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概念,并且有了判断“国”是否可爱的能力。这得长到一定年龄、接受一定的教育才行,起码要受过高中教育。有的人没有受过教育,可能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国家,那么,这条价值观对他(她)有什么作用呢?还有“敬业”,没有职业的人怎么敬业呢?现在有那么多人下岗,那么多人找不到工作,想敬业也无“业”可敬,这一条也没有普遍意义。另外,怎样界定、谁来界定“爱国”、“敬业”?也是问题。我觉得,作为个人行为上的价值观,目标应低一点,要适合每一个人,要提出一些做人的底线一类的东西。中国儒家传统,对人的要求就很高迈,譬如,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这个目标太高了,做到这九思,是君子,是圣人,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对于普通人,有没有更具底线意义的标准?似乎没有。提那么“高大上”的东西,却做不到,要么这些东西被敬而远之,与己无关,要么流于口号,成为空话,使人变得言行不一。与儒家的要求相比,佛教就有一些底线的要求。譬如五戒:“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饮酒”,就属于行为的底线。“不杀”这一条,你可能会说:“不杀人不就行了,这太容易了。”其实也不容易。不伤害他人的生命,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守得住吗?当有人惹怒了你,当有人对你说“他是阶级敌人”或“他是卖国贼”时,当你处在一个正在向某个生命施暴的群体中、你不施暴你就会受同伴的指责时,你还能守住这一条吗?在文革中,还有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许多人就是以崇高的名义,或受到崇高名义的召唤而施暴,没有守住这个底线,或者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底线。
再如“不盗”这一条,要守住也不容易。“不盗”不仅仅是不偷、不抢,凡是得到了不应当得的,就是“盗”。眼下揭发出的那些贪官,头一天还在做反腐倡廉的报告,第二天就被双规了。然后入狱,然后是痛哭流涕地反省自己腐败的原因:“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之类,净是喊口号。其实,他在台上喊那些高大上口号的时候,连底线都没有守住:第一,受贿了,贪了,得了不义之财,这是“盗”;第二,受贿了,贪了,还大喊“高大上”的口号,这是不诚实,是“妄语”。另外,他包养了那么多情人,就是“淫”。他要是真的反省自己腐败的原因,不需要“改造世界观”,只要看看做人的哪些底线没有守住就行了。一个人可以不爱国,也可以不敬业,可以做不成君子,当不了楷模,但必须守住做人的一些底线。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今日的教育以及我们设计出来的价值观,都有“理想高迈,缺少底线关注”的问题。这就出了大批只会喊口号,守不住底线,或不知道做人底线在哪的人。既然佛教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我们在思考价值观时,不妨也吸取佛教的一些东西,概括出一些对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任何情境中都应当守住的“底线”,以弥补儒家传统的不足。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部分。
对外交往价值观的设计
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从逻辑上讲,还应有一个国际层面,但很遗憾没有。对外交往也应有一套价值观,它是群体价值观的一部分,是这个群体怎么看待世界、怎么与其他族群相处的一套价值取向。对外交往层面的价值观和个人层面的价值观不一样,个人层面受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规范约束,但国际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制定对外交往的价值观,必须寻找对任何国家打交道都适用的价值观,这恰恰才是真正需要设计的地方。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缺这个东西不行。现在,在对外交往价值观方面,中国是很被动的,西方能够主动打出他们的外交价值观,如自由、民主、人权,中国却拿不出一套东西应对,只有招架,没有还手之力。我们只是说,你们这一套,只是幌子。这不全对,他们的外交价值观,反映了他们对世界的判断,反映了他们期望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其中也体现了我们人类积累的一部分经验。我们应当阐述我们的国家间交往的价值观,阐述我们所期望的世界愿景。中国外交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不是对外交往价值观呢?也是,但不完整。五项基本原则是操作层面的,这五项基本原则,体现了传统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少管闲事”,而仅仅这些,在今天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一套完整的对外交往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必须能回答在以下四个方面我们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即“终极关怀”、人、国家、国与国关系。这方面的设计,可以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借鉴西方现代国际秩序的一些价值理念,把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吸收进来。
设计中国对外交往值值观,需要考虑中国以外的情况。这里,我想讲讲日本的情况。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和前首相麻生,在外交上接受西方价值观,提出“价值外交”来对付中国。但日本的外交就是按照他们所说的价值观走的吗?不是,所谓“价值观外交”,仅仅是一个工具,一个“幌子”,而且,这个“幌子”直接从西方拿来,连改造工作都没做。在日本,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做法。前民主党首相鸠山尤纪夫,提出过不同的东西。他考虑了东亚的传统价值观,做了一些创造。他强调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性,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几个原则:博爱、自立、共生。我对他提出这三个东西评价甚高,当时我说,这几个东西我们应该接过来,作为设计我们外交价值观的参考。“博爱”是西方的概念,但它回答了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自立”这个词最初可能是日本人创造的(我没有考证),既有“独立自主”的含义,又带有传统东方的文化特点,包含着相互尊重:你是自立的,你有你的生活方式。“共生”这个概念也很好,它比现在的用的“和平”概念更具有东方智慧。“共生”包含着和平思想,但和平概念不包含共生思想。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概括和提炼,同时吸收西方价值观中带有普世性的东西,设计出我们的对外交往价值观。我初步想,“仁爱”是我们传统中一个很好的概念,可代替“博爱”,体现在我们的对外交往价值观中,以表达对人的终极关怀。还有,“人道”概念也不错,它既包括了西方的“人权”观念,又具有东方文化的特点,表达是对人的关怀。“自主”和“共生”这两个概念也可以考虑,前者是对国家的关怀,后者是对国家间关系的关怀,二者并提,还表达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合而不同”思想。这样,可考虑提出“仁爱、人道、自主、共生”,来作为我们对外交往的价值观。这一套价值观要高于西方的外交价值观,可以作为我们核心价值观体系的补充。
有了这一套东西,我想至少能起两个作用。首先,可能会在具有共同文明基础的东亚国家中引起某种正面的回应和共鸣,提供某种文化上的凝聚力。这一组价值观,在日本、韩国等东方文化传统中都能找到支撑。至少,它与日本民主党提出的一些理念相契合。提出这一套价值观,有助于东亚国家的在价值理念上的融合,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的展开,缓和或者减弱那些过于强调民族国家,过于强调现在国际秩序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
提出我们对外交往价值观还有一个作用,即为未来新的国际秩序提供我们的设计理念。西方国家不是动不动就打“价值观外交”牌吗?那好,我们也有我们的牌,而且,我这张牌,明显优于你那一张。如果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能按照我们这一套价值观打交道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更好的国际秩序,眼下现代国际秩序产生的种种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现有国际秩序源于西方,要设计一套国与国打交道的价值观,改变现代国际秩序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借鉴非西方国家的文明经验。中国应该做这个事情。日本要做这个事情,有其不足:它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经验的积累,近代以来又迅速、完全地内化了现代国际秩序,彻底成了西方国家的一员,失去了对现有国际秩序思考的立场和为新国际秩序提供价值理念的机会。中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明经验的积累,能够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近代以后又被排斥在现有国际秩序之外,今日也并没有完全融入这个体制,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它有相对独立的立场,有为新国际秩序提供价值观的机会。我不同意恢复过去的朝贡体制,事实上也做不到这一点。朝贡体系的存在是有一定条件的,如,过去只有中国单方面强大,其他国家无论是硬实力、软实力都很弱小;人员基本不流动、信息不发达、国家间交流活动极少,等。现在这些条件都不存在了,朝贡体系的崩溃是必然的,现在要走回头路也是行不通的。现在是信息时代,是文明融合时代,我们自身也从西方文明和现代国际秩序中获益良多。所以,只有在充分理解今日国际秩序的长处和短处,借鉴我们文明中好的经验,走文明融合的道路,中国才能为这个世界贡献一套在新秩序下国与国打交道的价值观。
讨论部分 (尚会鹏)
文化的变化与不变
我来回答一下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文化变化问题。现在对文化的研究,趋向于把文化和文明分开来看。古典的文化概念,如英国E.泰勒的概念,是大文化概念,几乎无所不包,跟文明同义。但现在趋于分开,一种是文明,一种是文化。文化指人们行为背后的原理,文明是在这种原理下的“造物”。我们掌握行为原理,主要不是有意识地从书本获得,而是靠无意识,靠生活中的模仿、耳熏目染。从我们吃奶的时候,妈妈就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这就是文化。这样就可以解释,文明是变化的,而且变化很快,在很短时间会成长、衰亡,但是人们行为背后的原理,即文化,类似于生物基因,会“遗传”。生物体已经死亡,但下一代在行为方式上仍与父母辈有类似之处。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一代一代是有连续性的,这种连续性,是一种类似生物体基因的东西在起作用,这就是文化,或可称作“文化基因”。所以,文化即便有变化,也是类似于基因突变那样的,十分缓慢,它跟文明变化不一样。
文化的先进与落后
接下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即文化的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判断问题。对于文明,我们可以分出先进与落后,譬如,工业文明,就比农业文明先进。先进文明使用先进的技术,制造出先进的器物,故可分出先进与落后。但作为人行为背后原理的文化,是不适合分出先进与落后的,因为,形成一种行为原理,就像生物体的进化一样,是适应特殊的生态和社会环境的结果,是不好分出先进和落后的。你不能说猫的爪子,就比螃蟹的钳子先进,因二者是适应不同环境进化的结果:猫的爪子适合在地上捉耗子,螃蟹的钳子适合在水里抓小虾。在文化人类学领域,有一种观点,认为所有文化都具有相对性,不能简单区分先进与落后,指的就是作为“行为背后原理”的文化。那你说,难道过去猎头民族、食人部落的陋习,也不能说是落后的吗?请记住,我们评判先进与落后,背后都有一个参照坐标,譬如,我们说,猎头民族、食人部落的做法是野蛮的,落后的,中国过去妇女裹足习惯是陋习,是摧残妇女。当我们这样判断的时候,有一个参照系统,就是,人是有尊严的,人的权利是不能侵害的,妇女和男人都有同样的权利。可是,你想过没有,这个参照坐标是很新的东西,猎头民族、食人部落、过去的中国,都没有这个参照系统,或者说,他们参照的是另一种系统,先进与落后不就成了相对的了吗?其实,猎头这种习俗,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中国古代打仗,也有猎杀敌人首级的做法。猎杀人头,肯定是敌人的头,如果连自己的家人、朋友都猎杀的话,这个民族也不会存在了。如果是这样,那你说,他们猎杀敌人首级,这背后的原理,跟现代战争中击毙敌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还有,过去中国妇女裹脚习惯,现在来看,摧残身体,侵犯妇女利益。但不要忘记,“摧残身体,侵犯妇女利益”这种判断,是在今日的参考框架下做出的,过去中国人参照的不是这个框架。裹足行为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是为追求美而摧残自己的身体。那个时候认为女人小脚是美的,而人为了追求美,有时候不惜摧残自己的身体。现在不也是这样吗?女士的丰胸、瘦脸、吸脂、增高等整容行为,不也是在摧残自己的身体吗?我看,这背后的原理跟裹脚是一样的,只不过现在的手段更先进而已。
文明间的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是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像亨廷顿认为的那样,文明之间一定是冲突的?我说不一定。文明之间可能是冲突关系,也可能是合作、融合关系,这取决于文明的性质,取决于人们怎么看待族群、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有的族群认为,族群之间应该保持和睦关系。近代以前许多部落之间,也能保持和睦关系。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过去几千年中就不是冲突关系。一神教文明比多神教、泛神教文明,在处理族群关系上,更具有冲突的性质。个人社会比“间人社会”(人的基本存在系统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关系密切“关系体”),在处理族群关系上,更具竞争、征服的特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有其文化背景,可以说它体现的是一神教文明下的个人社会在处理族群关系上的价值取向。
中日战争认识问题
我也来谈谈中日之间的战争认识问题。我曾在日本做过一个演讲,题目是“中国人的受害心理”。日本人说,中国人怎么老是揪住战争问题不放?我说,日本是加害者,中国是受害者,从心理学上看,加害者和受害者心理是不一样的。你打了我一拳,不久你就可能忘记了,我却忘不了。我对日本人说,你们了解吗?在我的老家河南开封县,县志上记载,哪年哪月哪日,日本兵来到村里,欺负了一个女孩子,被当地人打死。日本人派兵血洗村庄,把村庄中没有逃走的人全部杀掉,把村子烧掉。这件事就记在我老家的县志中。我说,你们先不要抱怨中国政府的爱国主义教育是煽起对日本仇恨,先去看看这些县志的记载。你们是加害者,当然会忘记,但受害者会忘记吗?你们要到中国去看看,看看你们祖先犯下的罪行对中国人造成的创伤,理解受害者的心理。
但是我对中国在战争认识问题的做法上也有一些看法。我们是战争受害者,在跟日本打交道的时候,有道义上的优势。譬如打官司,我是受害者,你得赔偿我,向我道歉,这就是道义上的优势。但我们要用好这个优势。刚才方教授讲,希望中国人能像基督教徒那样,宽恕加害者,我不太同意。没错,基督教徒能做到,打他的左脸,他伸出右脸也给你打,但这是一种宗教境界,是接受某种宗教教育、相信有一个更高的裁判来处理这个事情,才能做到这一点。你不能用宗教的标准要求中国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还是要按照世俗的办法解决:杀人者,做坏事者,要受到惩罚。但我们现在的做法,我认为还是狭隘了一点,狭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仅仅把受害的历史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手段。其实,这不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战时日本犯下的罪行,不仅仅是对中国的罪行,它是一种反人类罪行,我们要提到反人类这个高度来认识。我们记住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不是揪住不放,不是复仇,而是要以我们受害的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类的错误行为会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和痛苦。你们日本作为加害者,更应该总结教训,记住对人类犯下的罪行,看看一个民族在错误道路指引下,能做出多么残忍的事情来。我们人类是会犯错误的,日本犯过错误,德国犯过错误,每个民族都可能会犯错误。将来的中国弄不好也会犯错误。但你们祖先犯下的罪行,为人类提供了教训,提出了警示,我们从你们祖先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中,也从我们受害的亲身经历中,得到体认,今后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加害行为和中国人的受害经历,都是人类的一种宝贵的经验教训,加害者和受害者应当共同来为人类总结经验教训,这才是“以史为鉴”的真正含义。如果站在这个高度,我相信,不仅能够很好地利用我们的道义优势,还能够得到世界更多的人,包括那些杀害过中国人的后代的赞同。但,如果仅仅把受害经历用来作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加害者,可能还有大量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的人,会认为,你们是在利用你们的受害经历,宣扬复仇。
[ 尚会鹏 南亚、日本问题专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9月11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新浪博客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异同与价值标准」研讨会的演讲修订稿 ]
2014-9-15
中评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