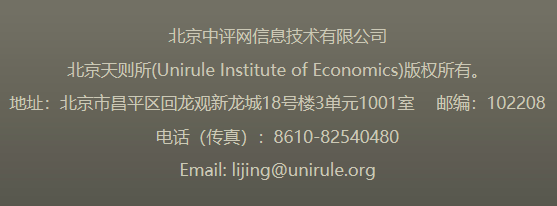今天,我讲的主题是关于出版自由。前些日子写了一篇评论《读马克思论出版自由》,发在FT中文网和共识网上,今天想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出版自由也就意味着思想自由,它的反面就是思想专制主义。中国历史上缺乏思想自由的传统,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以外,到了秦朝,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时期又大搞文字狱,就连毛泽东也说,历代都行秦政治。当时有不准妄议朝政之说,妄议朝政是要革职和杀头的。所以,思想专制主义在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
近代以来,自由民主的潮流浩浩荡荡,中国也受到波及和冲击。比较而言,民国时期好像思想自由的空间大一些,那个时候的大学就比较自由,北大30岁就可以当教授,外面的人可以随便去听讲,清华有四大名教授,西南联大的空气也比较自由。其所以如此,不是说当时的政府不想控制,而是没有力量,他控制不了。事实上,国民党到台湾以后,新闻出版和思想控制很严,以至发生了《自由中国》事件,雷震交军事法庭审判,直到1980年代末,特别是1992年开放党禁报禁以后,才有了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
大陆1949年以后的情况,思想控制很严,根本无什么新闻出版自由可谈。1978年以前的30年,我们的报纸、杂志、书籍、电台,到处重复着一个谎言,说美国、日本、香港、台湾,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救,拯救人类。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欣欣向荣,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美好,我们也以救世主自居。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大家出去一看,美国、日本、台湾、香港都比我们发达,人家过得比我们好得多。
由于实行新闻出版控制,没有思想自由,真相被掩盖,历史被歪曲。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发生了大饥荒和大危机,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人们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时间,人们才从非正式渠道知道了这些情况。在当时饥饿、肤肿相当普遍,饿死人不能讲,一讲就是反革命,饥饿成了思想问题。今天,这些历史和档案仍然尘封着和掩盖着。谁现在要讲这个问题,公开这段历史,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除非良心叫狗吃了,才会讲这个话。
实际上,1957年的反右就是一次新的文字狱,庐山会议就是不准妄议朝政的现代版,至于文革,思想专制主义达到了顶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自由多了一些。经济自由大大改善了,私有财产合法了;户籍制度松动了,人们可以自由流动(不是自由迁徙)了;思想自由也有了一些,至少在私下可以随意说话了。但自由仍然有限。那些话能公开讲,那些话不能公开讲,那些文章能发表,那些文章不能发表,那些书能出版,那些书不能出版,都是有管制,要审查,得批准的。至于个人办报、办刊、办电视,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开放。网络虽然是个虚拟的自由世界,但网络公司还得听网管的。叫你删除,就得立即屏蔽;你不删除,网管就给你删除。如果再不听话,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这类事情也是魔高一尺,道 高一丈,高手学会了翻墙,只是可怜了不会计算机的人,或者会计算机但不精通的人。
历史上不准妄议朝政,最近又有不准妄议中央之说,不知道什么叫妄议中央,与不准妄议朝政有什么区别?有关官员用民主集中制来解释,恐怕有点不伦不类。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原则,不是思想原则,组织需要服从,思想需要自由。中央决定了的事情要执行,还要继续讨论,因为决定有可能错误。议论就是检验,就是监督。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决定就错了,不仅不准公开议论,连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也不准议论,结果是造成了大饥荒和经济危机,饿死了那么多人。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决定了事情就不能讨论、不能批评呢?只有议论,才有可能发现错误的地方,才有可能纠正。
马克思在评论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时,对出版自由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 出版自由本身就是思想的体现、自由的体现,就是肯定的善”。马克思讲得多好啊!仔细想一想,如此,没有出版自由,其他自由也谈不上,因为各种自由是相互关联的。一种自由受到限制,另一种自由也会受到限制。所以,没有出版自由咱们就没有思想自由,你看到的都是歪曲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用这类歪曲和虚假的东西加工出来的东西就会更加歪曲,更加错误。
马克思还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说得多好啊!大自然的确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人类社会也是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思想和精神更是五光十色,纷呈异常。然而咱们却实舆论一律,思想统一。这就太荒唐了,如果做不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中国的社会进步将会遭遇到非常大的障碍。
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应该使出版自由和思想自由能够有一点前进。在突破这一点上,学界的人应该用力。当然了,这个事情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决策者和控制者想不想放,会不会放,能不能放,另一方面是学术界和出版界以及其他被控制者怎么做,怎么争取。我们当然要求放弃思想专制主义的一系列作法,开放言论自由,开放出版自由。因为出版管制不光限制了我们,也限制了他们,比如,邓力群鼓吹和实行思想控制最坚决的人,他的《十二个春秋》也拿到香港去出版了。这不是极大的讽剌吗。
从学术界来说,我们不仅要积极争取出版自由和学术自由,而且要警惕和清除自己思想上那些专制主义的东西,因为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有些东西已经渗透在血液里,需要来清理。比如,学术创作本来是个人的事情,由个人作主和个人负责,其他人可以建议,可以批评,但不能强令人家接受和采纳,更不能搞什么组织讨论和组织决定。我们作为主张思想自由的学者人,不要出一些控制思想的馊点子。在出版言论的自由方面,思想更开放一些,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点,努力推动落实宪法35第条。当然,这件事情还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谢谢!
[ 张曙光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2016年1月8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主办的2016「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转载请注明 ]
2016-1-18
中评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