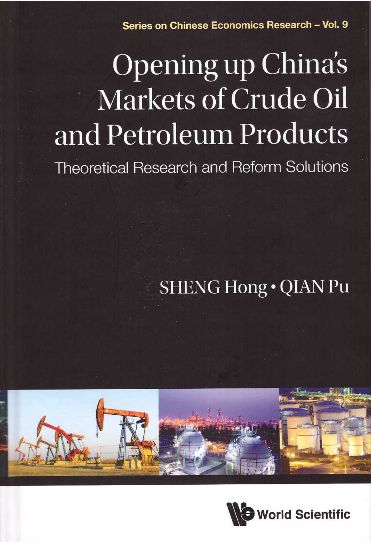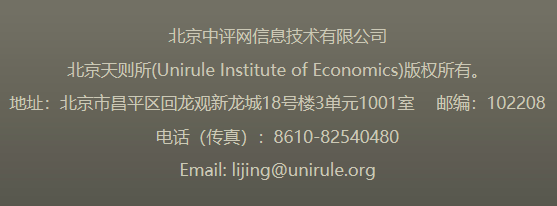盛洪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著有《为万世开太平》、《分工与交易》、《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治大国若烹小鲜》、《经济学精神》、《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和《士志于道》等书。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等。
《天道与神意》之宪政主义的儒学起源
在中国,很早就有超越的最高原则的观念,即“天道”;也可以称之为“天”,“道”,或“天理”。这种观念的文字,最早可在《易经》中发现,继而在《尚书》中多有使用。《尚书》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在古典意义上,“道”就是超越的。
到了老子和孔子时代,“道”就是一个很成熟的概念。在老子的《道德经》中,“道”是篇名,也是开篇第一个字。在这里,“道”是宇宙万物之始,也是它们生成、演化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却看不见摸不着;人中之君子可以知道它的存在,竭力探寻和追求它,却只能获得大致的轮廓,得到一些片断。
所以,“德者,得也”,即“德”是人们尽其所能对“道”的窥见和感悟。正因为,道是浑然一体,混沌难辨,无声无色,高深莫测,理性有限的人类就不可能全部把握,他们的政治领袖也不可能。所以,这些“君”和“王”只能尽量探究道,追随道,按照他们理解的道去治理社会。而老子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在说,一个政治领导人怎样才能更接近道地去履行职责。
在《论语》中,道与人的分野更为清楚。在这里,孔子经常用“天”,“道”,“礼”,“仁”,“中”和“义”等来表示道,在其中,“天”可能是最为贴切的表达。天既是全知全能的存在,又是最高的正义;而人间社会的君或王,只是世俗的和有限的政治领导人。即使是最高的政治领导人,天子,也不过是人间社会中的一个公共职位(天子一爵)。他们要保住这个职位,就要把握天道,遵循天道去施行公共治理。
如果不能把握天道,甚至违背天道去滥用公共权力,就会失去这个爵位,谓之“失天命”。这个概念诞生得很早。《论语》中记载尧向舜交班时说的话:“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好好干,让老百姓穷困的话,上天就不再发你工资了。后来当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时,都涉及到天命的转换。其原因,就是失天道者失天命,得天道者得天命。天命就是统治或公共治理的合法性。
反过来讲,一个人或集团并不因获得了政权或政治领导人的世俗地位就有绝对的统治合法性。当他们的统治和治理符合天道时,他们才有统治合法性,当不符合天道时,就没有统治合法性。这被有些学者称为“君权有限合法性”(邓小军,1995,第286~292页)。这种观念,也贯穿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当一个政治领导人行仁政,替百姓着想,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换民众的幸福,并能约束自己时,则被称为君或王;当昏庸无道时,就失去了君或王的资格。所以孟子评论武王伐纣时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这是很清楚的政治合法性判断。
到了汉代,董仲舒将先秦的道家、墨家和儒家有关天道的思想提炼为“天”,并赋予天某种准人格神的性质,用来作为政治集团统治合法性的衡量标准。他说,“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后可以为王也云尔!”君主的政治地位虽在一般臣民之上,但仍是天之下的一个凡人。所以“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与先秦天道主张的区别是,君主遵从天道,不仅要在法度道德上顺应,而且要用明确宏大的仪式显现出来,“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如果君主遵循天道做出成绩,上天会降下祥瑞;如果做了违反天道的事情,上天则会降下灾异:“灾者,天之谴;异者,天之威。”因而,董仲舒的“天”是“为制约君王权力寻找形而上的、神圣的论据。”(曾振宇,1998,第90页)
到了宋代,天道多被称为“天理”。宋儒探究天理,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挽救“宪纲危机”,这起源于“帝王存心之偏导致政治方向之误”(卢国龙,2001,第314页)。解决的方法,按王雱的主张,就是“任理而不任情”。所谓“任理”,就是“一种政治宪纲或方针”,“也就是将天道理解为无意志、无情感的自然法则,从自然万物的大化流行中寻绎出普遍原理,作为人事的准则。”(卢国龙,2001,第181页)。
不言而喻,这种看法把世俗政权中的君主看成是易犯错误的凡人。程颐在《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书》中批评说,宪纲危机的根源在于皇帝“以天下徇其私自欲者也”。解决的方法,就是皇帝要遵循“大中之道”(卢国龙,2001,第313~314页)。这是指自尧舜禹开创的儒家道统,而后者就是儒士们追求天道的结果。因而,“大中之道”就是天道。也就是说,要用天道来衡量政治领导人的行为与举措,如果违背天道,皇帝就要自我反省,“格君心之非”(卢国龙,2001,第325页)。在宋代,对君主的批评不仅通过上书,甚至可以当面批评。据记载,朱熹在任宋宁宗赵扩经筵讲官时,曾当面要求皇帝要“正心诚意”,明确提出“防止君主独断与近习预权之法”,被评价为有限制君权的意义(束景南,2003,第981页)。
到此可以很明确了,中国的天道传统一直包含了形而上的超越的天道与世俗政治领导人有限性的鲜明对应,并建立了由天道衡量政治合法性的宪政标准,从而形成了一种天道在上、政治在下的宪政结构,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近代。余英时指出,“知识分子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余英时,2003,第93页)
在政治实践中,通过革命废除无道君主,只是天道显现力量,纠正世俗政权错误的最后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最后结果是迫使君主或其它形式的政治领导人遵从天道的有效威慑。迫于压力,任何政治领导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合法性都力图了解天道、把握天道。然而,“天道”高远,如何知天道?《尚书》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一个凡人或世俗政治领袖可以有一个简单办法,即通过民众的感受和表达去接近天道。
然而,民意还不完全等于天道;当下的民意表达也可能只关注民众当下的和局部的利益。所以《尚书》云,“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对于更为一般化和持久的“民意”,即人性的探究就自然是一个重要补充。在这方面,儒家把人性作为天道在人间的完全体现。孟子曾说过,“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中庸》又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都是说,人性就是自然,自然就是天道。人们可以通过对人性的了解去感悟天道。
而人性的本质是善的,即孟子所谓人有“善端”,“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是本性自然的。但可能随着自我利害意识的加强而被遮蔽。有些人可能会一直保持着这个善端,有些人可能要通过学习而重新发现和确立。而一些人不遵循这个善端去作恶,是违反人性的。而这种善,就是“各正性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使得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能在不损害他人情况下获得自身幸福的天道规则。
人有善端,也有理性,因此可以自治。这在中国文化传统语言中,表达为要求统治者的无为,即如老子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自治的范围,就是民权。所谓“权利”,就是受保护的利益的恰当范围。英文rights,就是“恰当”之意;拉丁文Jus,也有规范与正义之意。因此,对应于现代汉语“权利”的古文,一个字是“所”。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中“所利”即恰当利益之意。在《礼记•礼运》中的“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章句中,“所”和“有”都有“恰当”之意。
更直观地,是“经界”一词。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即指权利的边界。他接着说的话就更能证明,他是指权利边界的:“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孟子•滕文公上》)更一般地,“礼”是用来泛指包括权利边界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均衡,政府侵犯人们正当权利的行为就是“非礼”,如“初税亩,非礼也。谷出不过藉,以丰财也。”(《左传》)
就这样,既有善端,又有理性,还有权利的人们组成了社会和国家,就是后者的基础和目的。孟子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正如夏勇所说,“本者,主体也”,“民惟邦本”就是“一个关于人民主体资格的判断,还是一个关于政治合法性的判断。”(夏勇,2004,第8页)也就是人民主权之含义。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很显然,民是目的。
就这样,从超越的天,到可窥探天道的民意,经过文化精英对一般的和持久的民意,即人性的探讨,得出有关人的善端、理性和权利的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和目的,建立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进而,超越自己利害、关心社会与历史的文化精英,通过对不同制度规则的得失成败的历史积累的观察,提出通行于人类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一般原则,就是弥补民意之缺陷,更为接近天道的努力。更进一步,天道的概念,作为文化精英和政治统治者追求和探究的最高正义,则是反衬人类理性之有限和世俗政权之粗陋的超越且神圣的价值,使得他们心怀畏惧,承认对他们的制度约束,成为传统中国的宪政主义的精神基础。
(全文链接: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2943)
相关文章:
《传统中国谏议制度的宪政含义》
《论儒家宪政原则的历史维度》
《宗教人及其制度含义》
《视野与计算》
《天下文明》
旧邦新命何处寻?新儒门下听分晓。天则书院•新儒名家讲坛即将开始:
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3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