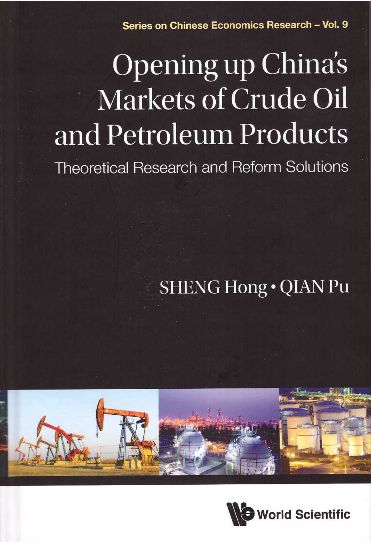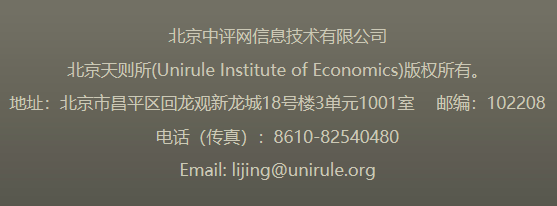姚中秋(秋风) 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弘道书院山长。著有《华夏治理秩序史》卷一、卷二,《重新发现儒家》,《国史纲目》,《儒家宪政主义传统》,《嵌入文明:中国自由主义之省思》,《为儒家鼓与呼》等。
大陆儒学之新气象
(转自儒家网 http://www.rujiazg.com/article/id/6062/)
接《天府新论》编辑赵荣华君信,嘱为该刊2013~2014年刊发之儒学文章汇编作序。检视目录,自己名字数次出现,写一点文字以襄盛举,义不容辞。
在接到此信前后,应邀为杜维明先生新著《二十一世纪的儒学》撰写书评,即发表于《新京报》的《儒家义理是一套世界公民语言体系》,其中两段,或可表达我拜读这个文集的心情:百年来,中国学人信心尽丧,在思想、学术上自甘为奴,包括新儒学的诸多努力,也只是身处绝境中的勉强防御而已,其论述模式不外乎:西方有的,儒家其实也有,只是不够充分,可在西方刺激发展。姿态如此卑下,其思考也就只是让儒家向西方靠拢,历史仍将终结于西方的宗教、价值、制度。儒家内在的伟大价值被取消了,中国之道终究要被抛弃。如此心态,儒学其实难说发展。杜先生则转奴为主,立足于儒家,观世界之众生相,思考普遍的拯溺之道:见世人之迷于物,而提出精神性人文主义;见神教之过于执,而阐明和而不同之大义;最终确立仁为普适价值。儒家内在价值凸显出来,这价值是普遍的,不仅解决中国问题,更解决世界问题。有如此对世界敞开的天下情怀,儒家才有发展之契机,也才有存在之理由。
在港台新儒家中,钱宾四先生和杜维明先生的经历、见解较为独特:
宾四先生完全立足中国学问,而所持之论,无不清明开通;尤可惊异者,先生凡涉西方之论说,无不暗合西方贤哲,而更为平正高明。先生之学,随时间推移,反而更见其可信、可贵。先生不仅坐而论道,更兼起而行道,在香港殖民地创办新亚书院,守护和弘扬中国文化。
杜维明先生经历与宾四先生正好相反:多数时间任教美国名校,与欧美、印度、伊斯兰世界贤哲广泛交游。此亦为行道之方。正是在此广泛而深入的文明对话中,先生慧眼独识于孔子之道和中国文化之精微、卓越之处,并坚信,孔子之道实可普适于人类。
大陆新儒学承接了钱先生、杜先生的自我肯定态度,而《天府新论》近两年所发表的文章,最为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是这个文集最可注意者。
今日大陆儒学约有两个源头、两种学术范式:第一个源头是现代新儒学,第二个源头是康有为的政治儒学,而为蒋庆先生重新揭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新文化运动催生中国思想之觉醒,现代新儒学兴起,主要表现为援西入儒的哲学构造。只不过,1949年后,此一传统出现分叉:留在大陆者,被迫退化为中国哲学史,如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之学,在学院内根深叶茂。另一支去往港台、海外者,继续保持哲学样态。八十年代后,以港台新儒学名义回流大陆,产生广泛影响。
此一系统的大陆儒学,上焉者,以西方哲学诠释儒家思想,下焉者,仅对儒家作哲学史的考察。理论上的关注点是心性;进入现实,所关注者仅为文化。社会、政治、国际等领域的制度,不在其关注之列。
这一关注点受制于其关于儒家于当世之价值的判断:西方代表了知识、制度的现代、先进,儒家只在心性、价值上略有价值。塑造人间秩序之种种制度,儒家已无力发言,西方所创制者就是中国所当行者。因此,现代新儒学所做的哲学努力是转化儒家,令其心性之学有助于西式制度在中国落实,所谓“良知坎陷”,所谓“创造性转化”,所谓“抽象继承”,无不措意于此。
究其实,在此思考方式中,儒家是文化上的负担。当然,在解决人类精神问题上,儒家似有可取之处,但在制度上,儒家已属多余,甚至反动。而现代新儒学又普遍接受西人看法:制度至关重要,制度带来一切富强、民主等好东西。这样一来,总体上,儒家不过是未来即将成立的现代中国的一个点缀,根本无关紧要。儒学于今日要做的工作无非是自我改造,以迁就西人创制之现代制度。至于儒学对于世界,当然全无价值。
儒学之现代史实始于康有为,康氏立足公羊学,接纳西学,而发展出儒家现代创制立法之说。但此学长期中绝。蒋庆先生于90年代上接康有为之思想范式,相比于学院主流的狭隘儒家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不仅极大拓展了儒学之研究范围,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走出上述范式中儒学自我否定之陷阱。蒋庆先生断言,儒学不仅有能力安顿心性,更有能力筹划各种制度。儒学是整全的,因而是自足的。儒学完全有能力在中国完成优良秩序之构建,西学尽可发挥补充作用。
中国知识人在过去一百年积极构造的思想上的主奴关系牢笼,轰然坍塌。因此知识上的起义,过去十年来,大陆儒学界发生了一场精神革命:大陆儒学从自我否定意识中解放出来,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
现代新儒学大约诞生于百年前,于今日,终于渐入佳境。《天府新论》编辑慧眼独具,近两年所刊发之儒学文章之作者,基本上出自获得精神解放的儒学者之手。还有很多儒学者依然在自我否定的框架中苦思冥想,寻找不可能的出路,而这本文集的作者普遍具有了儒家的主体性意识,由此可略窥大陆新儒学之风采。
首先,留心治道,无所不涉。
现代儒学在康有为那里,主要关注变法、创制。但晚清政治变动剧烈,儒者应对不足,导致儒学与政治逐渐脱节。在晚清立宪和民国成立过程中,尽管有些立宪者有道统意识,儒学本身却并未有效提供制度方案。大约只有孙中山先生留心于儒家治道之现代构建。
相反,在学界,现代新儒学传统中的儒学研究就是哲学式研究,或者哲学史式研究。宋明时代的著名儒者,牟宗三先生的思想,被大大小小的学者们,研究、写作了一遍又一遍,朱子、阳明的一个字、一句话,被反复考证、解读。而人们无从知晓,这些不断重复的探讨,意欲何为。
本文集所收论文,虽只有二十余篇,却涉及众多领域,基本上呈现了儒家之学的全貌:从心性,到教化,到政治,乃至于国际秩序。孔子行道天下,致力于重建秩序,由内到外,自近及远。关乎人间秩序的所有领域,都在孔子关心之列。孔子的思想,是围绕着治道展开的,是关于人、关于秩序的完整的义理体系。
现代新儒学拱手让出诸多领域,导致其学问之路越走越窄。晚近十年来,由于政治儒学之兴起,儒家进入广泛领域。大陆新儒学正在收复失地,重建儒学为一整全的义理体系。尽管所持之论容或生硬、幼稚,但全面覆盖,本为儒学应有之知识形态,儒学不能不走向广阔的知识世界,探索,冒险。
其次,通经致用,创制立法。
在孔孟荀那里,在董子那里,在程朱陆王那里,儒家之学不是纯粹思辨的哲学,也不是寻求救赎的神学,而是成己成物之学。儒者为学之目的,在成就天人之际的良好秩序,赞天地之化育。因而,儒学者不能不有行道天下之情怀,不能不有经世济民之用心,不能不有创制立法之抱负。
既往哲学或者哲学史形态的儒学,让儒学者无从切入现实,即便有心,也过于虚玄。由于缺乏足够具有感召力的现实论述,在大转型的舞台中心,几乎不见儒学踪影。
随着众多治道议题的展开,通经致用的儒学品质得以充分展现。由此,儒学者就不再只是书斋里的学者,而具有士君子之人格,敞开了实践的可能性。由此,儒学得以重新进入中国社会变革的舞台中心。儒学不再只是旁观大转型,而是引领大转型。唯有如此,儒家中国才有可能重现,而这是中国这个超大规模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命定的生命形态。
再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前面提到,新一代大陆儒家确立了自身的主体,但这绝不意味着,儒家固步自封。儒学从未自我封闭,夫子之教就是“博学于文”。历史上,儒学的每一次发展,都以吸纳、消化新知识为要务:汉代儒学吸纳、消化了诸子学;宋代儒学吸纳、消化了佛、老之学。但由这两次历史经验也可看出,唯有当儒家立定主体性,才有真正的学习,才有真正的创造。
过去百余年,凭借着物质之势,西学对儒学保持高压态势,中国学者震惧之余,忙于确立西学为信仰。于是,中国学人对西学之理解,始终停留在较低层次,概括西学为若干条简单的真理,信之不疑,且大胆地以之判断中国之学、中国之制。人们崇敬西学,反而无心深入了解西学。尤其是在儒学者中,对西学了解始终极为肤浅,比如,在儒学者的论述中,民主、科学两个词近乎神话。
然而,晚近二十年,中国学人对西学的理解逐渐加深。伴随着加深,笼罩在西学之上的神圣光圈消散。过去十年,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对西学有深入把握,反而转回中学,服膺儒学。这些学者入得虎穴,颇得虎子,不再视西学为真理,而以平和心态对待之。
至此时,西学才渐归正位,那就是“用”。儒学者从来不会自我封闭,但儒学者之博学于文,必坚持张之洞两甲子前提出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真正的学,以我为主的学,学的目的是为了丰富儒学,而绝不是为了自我改造,自我否定。
最后,心态从容,天下情怀。
百余年来,中国人充满焦虑:中国还能不能生存下去?相应地,儒学者充满焦虑,其中最强烈的是存在的焦虑:在现代世界中,儒学还有没有意义?儒学还有没有资格继续存在下去?还有没有可能发挥作用?现代新儒学就是在这样的生存焦虑中形成、展开的,焦虑心态清楚体现在思想、学术中:学者忙于“开出”,忙于靠拢,忙于论证自身的现代价值。可以说,在过去大多数时间,现代新儒学基本采取防御态势。
今天,儒家的焦虑大大减弱。由于立定了主体性,大陆新一代儒学者的心态普遍较为从容。因为议题丰富,儒家的精彩之处逐一显现,儒学者逐渐具有心性和义理上的双重自信,不仅能在自足的儒学框架中思考中国问题解决之道,而且能够从儒家角度评骘西方得失。
由此,儒学者真正具有了天下视野。从根本上说,过去百年的儒学,自我限定于民族主义的心智牢笼中,反复申明自己的中国属性,尽管这属性本身又引发自卑感。儒学者与整个中国知识界一样把中国特殊化,视西方之价值、知识、制度为终极的普遍性。自我特殊化的儒学者丧失了向来具有的天下情怀,反而深陷逆向普适主义心障中。
大陆新一代儒学者立定主体性后,真正具有了天下视野。儒家之学是整全的,并且是普遍的。中国自身的成长即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就是天下的第一步。于是,对儒家之道化成中国、中国持续成长之历史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而这样的研究又具有普遍的天下指向。
大陆儒学晚近十年逐渐形成的上述四个特点刚刚显露,且相当零散,而《天府新论》所刊文章,于两年当中就相当完整地呈现,可见编辑之有心、用心、尽心。这一册文章未必有传世之作,但足以展示今日大陆儒学之新气象,指示大陆儒学未来发展之大方向。儒学圈内外,可不珍之重之欤?
旧邦新命何处寻?新儒门下听分晓。天则书院《新儒名家》讲坛即将开始:
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3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