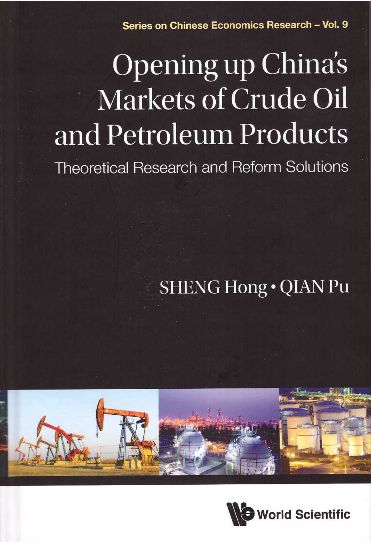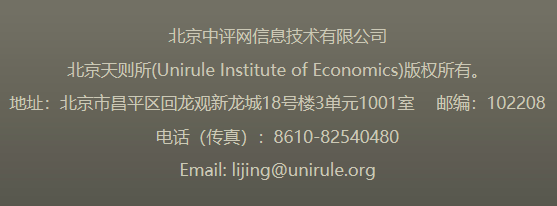任剑涛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山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著有《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研究》,《伦理政治研究》和《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等书。
天道、王道与王权——王道政治的基本结构及其文明矫正功能(节选)
(转自爱思想网)
王道:王道政治的合法性根据
天道为君王规定好了行使仁政德治的为政规范。因此,仁政德治便成为“为政之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仁政德治,也就成为王道政治的核心建构。就字面含义讲,王道,指的是为王的根本道理。从王道政治的逻辑推展来看,在天道为王道政治提供了高级法背景之后,王道政治经由关乎政治生活的基本理念(basic ideas)和基本制度(basic institution)的设计,开始向下落实为一套实际的、绵密的社会政治制度安排基准。
王道政治的“王道”论述,存在两个相关的论述进路:一是理想型的论述,就是孟子系统论述“王道”的王道政治思想;二是现实型的论述,就是荀子论述“王道”的王道政治思想。两者长期被人们视为具有高低境界之分的论述。在儒家心性之学的谱系中,孟子的论述被视为正宗,并且被视为合乎道统的言说。而荀子的论述则被看做是歧出之论,被排斥在道统之外。实际上,二者对王道政治之“王道”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论述,恰好构成相互依存的一物之两面:孟子的王道论述倾向于这一政治形态的合规则(norm)一端;而荀子的王道论述则倾向于合法则(rule)一端。两者结合起来,共同构成王道政治之王道的规范内涵。
首先,分析理想型的孟子“王道”论述。孟子对王道政治之“王道”即为政的基本理念与制度安排,有一个基于超越政治经验的理想型论述。这一论述,基本的理念结构是仁心与仁政的直接相通、内在延续。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
至于这样的仁政德治,在基本制度的设计上,体现为重视民生、界定权限、公私兼顾的施政举措。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这些制度设计,因为都是从“应当”的视角提出的,不是对现实社会中实施的制度举措的描述。因此,因应于自然节奏的“时”而生成的“养生丧死无憾”,正“经界”的一定之规和用之限制权力漫无边际的贪欲,以及查无实据的井田制构想对公私财产关系的规定,都体现出孟子对王道政治之“王道”制度规则的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而这一王道精神凸显的核心价值,就是周公开辟王道政治之“王道”论说进路时所彰显的基本精神——“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对王道精神实质的阐释,确实具有显见的理想性。因为建立在“不忍人之心”基础上的“不忍人之政”,因为源自人的、无条件地存在并发挥作用的善性良心,因此施政过程中的所有政治举措,也就围绕着仁政德治而展开。但也正因为如此,孟子的论述与实际的政治制度就有了明显的距离感。虽然这样的距离感是孟子得以彰显“王道”的理想性必须的条件,但离人们的经验感知确实比较遥远。见识悠远,但与政治疏离。一种以德性规范约束政治生活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在王道的阐释上,能不能更为贴近政治生活需要,同时又经验性地规范政治制度设计呢?荀子贴近政治经验的言说进路,似乎胜于孟子远离实际政治的理想化阐述。
其次,有必要分析荀子经验性的“王制”陈述。荀子对王道政治之“王道”政治制度安排,也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他对王道的四维论述,即对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的论述,将王道政治的制度精神内涵,全方位地凸显出来。
就王道政治之王道的基本政治功能而言,仁政德治所生发的政治亲和力、权威认同感和政治臣服性,是一个政治体实现其强盛目标、慑服对手和让人心悦诚服的前提条件。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荀子•王制》)
围绕王道的政治目标,王者的自我塑造、制度设计、审时度势和行事法度便相应显现出来,构成王道的基本制度精神之投射于四个维度的具体陈述。
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夫是之谓有原。是王者之人也。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
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荀子•王制》)
四者围绕“王者”这一王道主体,进行了系统的主体特质勾画:具有王者品质的人,必须是能够掌握政治运行根本道理的人;而行使王道的制度安排,必须尊崇相沿有致的制度规则;在行政过程中的精思明辨,是人心思定、社会有序的条件;而在实际的行政举措上,实行宽政,以身作则,堪称人师,四海钦服。荀子全面刻画了王道的王者主体特质,将孟子所期待的理想性政治,落实为具有经验性内涵的政治精神。一方面,荀子所指的王道,不出儒家王道政治以德性规范约束政治运作的总体精神方向。周公奠立的“敬德保民”的王道政治基本精神,在四个维度上都得到鲜明的体现。另一方面,荀子不再以虚构的井田制这类古制,作为王道政治制度设计的观念源泉,而是直接将王道的主体承载者的诸品行罗列出来,从而将王者与王道直接关联起来,将王道政治的实现期待,直接坐实于王者的权力实施过程。比较起来,孟子之为王道言说凸显的“不忍人之心”这样的内在良善之心的基础,似乎被削弱。但荀子却将“不忍人之政”的丰富内涵,系统地凸显在人们的面前。两相贯通,仁心与仁政的内在勾连及其仁政德治的政治操作状态,就得到系统的显示。
即使是孟子与荀子两人的王道论述具有承接关系,即荀子将孟子理想化的王道论述坐实为经验性的王道刻画,也必须承认,其中存在逻辑上的缺环:不忍人之心与不忍人之政,是不是君主个人品质的自然显现?假如仁心与仁政仅仅依赖于君主的个人道德品性,这种政治模式的不确定性,势必成为它的最大特点。只有在董仲舒的天道与王道的关系论述中,才能堵住这一漏洞。这并不是说董仲舒仅仅陈述了“天道”之于王道政治的决定性环节。他论说的重要性在于,天道与王道两个关乎王道政治的高级法与实在法的关联性,得到了极其明确的强调。事实上,“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既是天道与王道紧密相连的断言,也是王道根本精神的正当性保障。而这也是董仲舒据以成为王道政治完备性理论建构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的标志。这不是要神化王权,实在是在表达规范王权的意图。因为天道是“覆育万物”的,因此王道必是仁政德治的。由此出发,董仲舒所申述的天道对人道的内在既定性的规范,也就是重要的、规范权力的说辞。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董仲舒:《贤良对策》)
天道是王道的根源所在,天道“覆育万物”的特质不变,仁政德治的王道也就相应不会改变。这样的相关性论述进路,成功地填补了孟子与荀子仅就王道的道德内涵与政治内涵谈论王道,可能通向君王的道德专制的重大缺失。比较于人民主权的现代宪政体制来讲,其制度的现实有效性较弱,但限制权力促使其规范运作的意图并无二致。
王道政治之王道的制度取向,即是礼制政治。在合法性的所指上,是不是合乎礼制规定,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是否具有合法性保障的标志。所谓礼制,就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演变,从“大道之行”到“大道之隐”的迁移,显示了最值得期待的理想政治(ideal politics)与不得不承诺的政治理想(political ideas)之间的差异。
但“大道之行”前提条件下的“天下为公”,与“大道既隐”情况下的“天下为家”,并不是王道政治与反王道政治的划分界限。相反,两者都是王道政治的表现形态。不过前者乃是理想性的王道政治形态,它将天道与王道有机统一起来,将私利意欲完全升华为公共取向;后者承诺了私利取向之作为现实政治运行的前提,却以礼制的运行,保证了各归其位的古典公正秩序,进而体现了“覆育万物”的天道精神。在这里“大道既隐”不能被解读为“大道隐没”,而是作为大道的“天道”无法直接实现其理想政治状态,必须从现实政治处境出发,先行追求“小康”,进而才能实现大道所指向的“大同”目标之历史性演进的、由隐到显的政治过程的陈述。这也体现出王道政治的现实性特性。
由上可见,王道政治的合法性特质,与天道呈现的正当性状态,是内在吻合的关系。而王道政治的合法性特质,并不是简单的合乎作为中华法系的实在法规定的合法(legality),而是指合乎天道所规定的王权实施法则之法。这是对合法性概念的强势遣用。真正显现合乎实在法规定的王道政治构成结构,只能是从王权的实际运行机制上显示出来的。但王道之作为王道政治从天道坐实为王权设计的中介结构,是王权行使必须既按照王道的合法性规则、又按照天道的正当性规范来建构的刚性规定。因此,王权并不具有随意妄为的道德—政治—法律空间:王权的运作,就其最高最后的根据而言,被天道的正当性言说所制约;就实际操作而言,则被仁政德治的王道判准所衡量。